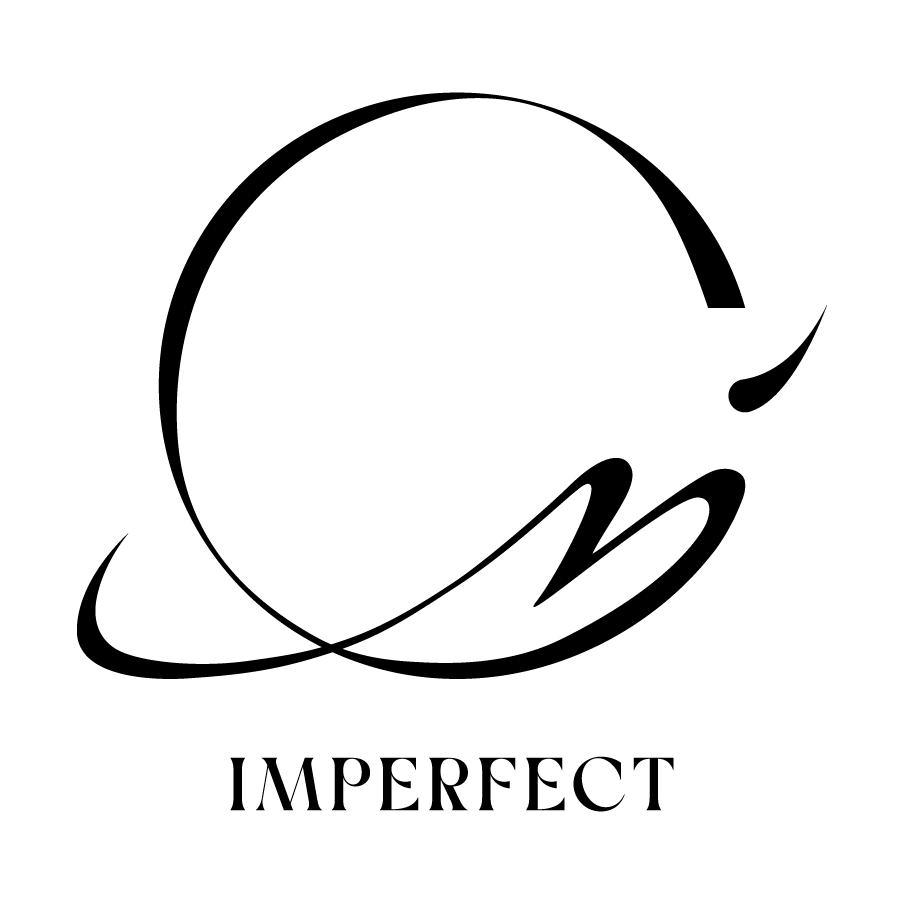看似瀟灑的說走就走,背後總藏著無人知曉的鬱結 ──《女人出走》
又往牆上貼一張明信片,素未謀面的教堂與山峰,如此在我家中佔有一角,豐腴的油畫女子側眼看我,彷彿問道:「你呢?你要去哪裏?」當我照著長長的行李清單收拾,從抽屜深處翻出證件,將洗髮水和沐浴露分裝妥當,或移居外地前爭論應否帶上電飯煲和枕頭,才驚覺不管是四日三夜的觀光團,還是沒有歸期的遠行,離開才是一切的開始。
這就是為甚麼,《女人出走》(Villa Amalia/台譯《亞美莉雅別墅》)幾乎用了一半的篇幅來交代女主角出走前的準備。劇情開首並不新鮮:法國影后伊莎貝‧雨蓓(Isabelle Huppert)飾演的鋼琴家安,撞見伴侶與外遇親吻,觸發她要拋低過去,到另一個城市隱居。伊莎貝眉目唇角中的清愁,裹在卡其色風衣中的單薄身體,你總覺得她在壓抑甚麼,內心用力踩著腳踏並向琴鍵傾注全身的憤怒,每顆音符卻像包上保鮮紙般,幽幽落在聾人的耳邊。換作是別的演員,治療情傷是恰當自然的解釋,偏偏是伊莎貝‧雨蓓,便覺得她的徹底出走,根本不需要動機,只是回應某把聲音的呼喚。
她的離開亦是這麼寂靜而決絕,平價出售房屋和汽車,燒毀照片、明信片和琴譜,衣服、手錶塞進垃圾袋扔棄,告別母親,甚至賣掉賴以維生的三部鋼琴,放棄巡迴演出的機會,不帶半點留戀。「說走就走」聽上去那麼瀟灑,但別忽略了切斷與一地的連繫,比想像中複雜得多:提取銀行存款竟有上限,封鎖電郵與電話亦不容易,而你離開之前更必須面對別人的追問:「你要去哪裏?」「為甚麼?」若像她一樣簡答:「只是離開。」注定要承受對方不解的眼神,唯有明確給出目的地,還有看似成熟的原因,譬如「要去美國工作」,才能令眾人心滿意足。
有人像我,在旅途上貪婪地蒐集,沿途將紀念磁石、形狀怪特的小石、餐廳的墊杯紙一一藏好,再用剩餘不多的手機儲存空間,留住旅館一隻貓的氣味和某位陌生小孩的眼神,務求滿載而歸。
而安每換一個落腳點,則將身外物逐件捨棄:脫去都市女郎的風衣,換上運動外套徒步山間,沉重的行李袋變成輕便背囊,曾經挽成髮髻的長髮,乾脆剪短,最後露出脆弱的脖子。來到意大利小島,只餘下薄薄的連身裙,舊的情人、舊的生活、舊的自己都遺落身後,越遠越是輕盈。但結局並沒有停在這裏,因為無論走得多遠,她始終還是過客,仍然要亮出護照來證明身分,在他人眼中,她仍帶著「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氣息。
移到地圖的另一點,不代表就能逍遙快活,解開所有鬱結。從前她在狹小泳池來來回回,如今把自己放逐到大海之中,最貼近自由的一瞬,幾乎淹死而無人察覺。別了台下掌聲,別了分擔寂寞的摯友,孤獨多次在午夜襲來,她驚醒過來,想著是否永遠都得不到幸福,那麼拋棄安穩生活出走的意義是甚麼呢?
這個問題太過宏大,可能追尋答案的過程,正是答案本身;可能答案也藏在她走過曲折的泥路,築在山崖上的紅屋映入眼簾的一刻:屋裏沒有字畫、鋼琴,只有一張陳舊木桌、一把木椅與一張床,灰牆粉刷拙樸,靠著弱不禁風的木架,無法與在法國的公寓相媲美。她伏案用一枝鉛筆畫出歪歪的五線譜,應驗了當日與買琴者的對答,亦是我最喜歡的一段對白:
「你不再彈琴了嗎?」
「當然還彈。」
「那為何賣掉鋼琴?」
「我可以用其他琴,甚至不用琴啊。」
來到遠方,拋棄了所有熟悉的事物,才會倍感孤獨,但與此同時,她才會在海風和筆觸的窸窸窣窣裏,聽到心裏最微細的琴音,是那坐在家中三角琴前,從未仔細聽到過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