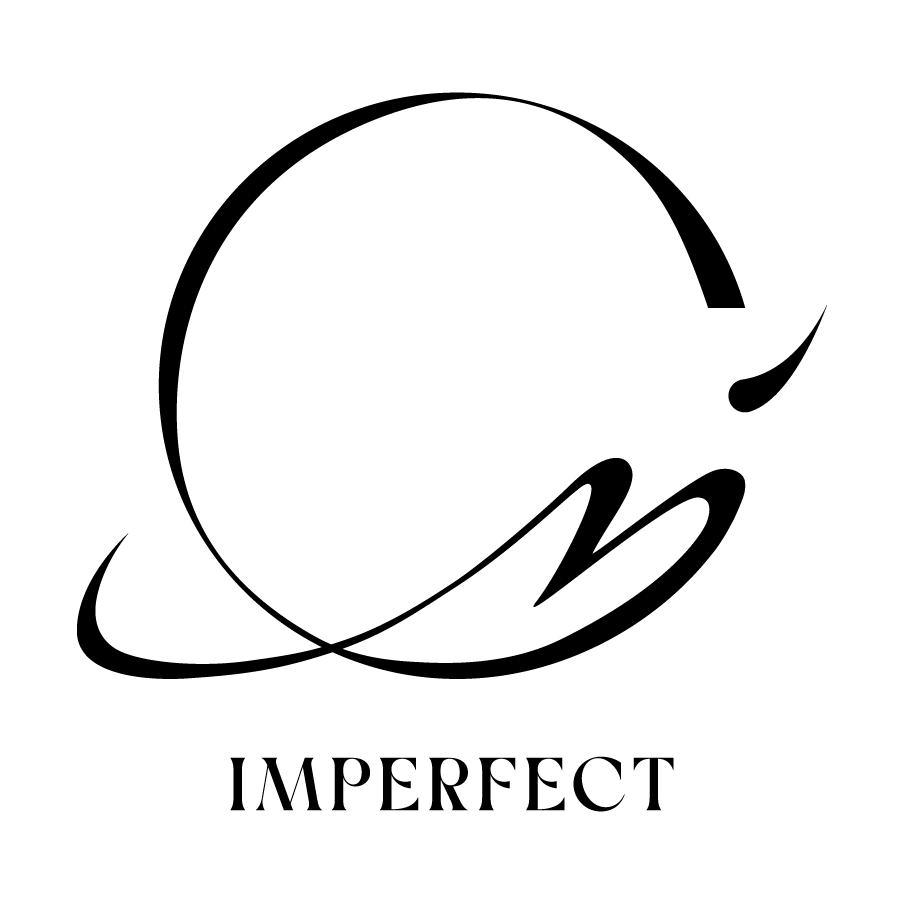我們都在不知不覺間,長成習慣吃苦的大人
我撿拾舊物的成就清單上,又添一項。2024 年末走在舊舖聚集的街區,低頭發現某戶人家緊掩的欄柵前,竟有一部被棄置的膠囊咖啡機,低調得幾乎融進昏暗暮色,上面貼了張紙手寫著「Works」。它不是甚麼昂貴專業的機器,但我反正連業餘愛好者也算不上,何況它彷若憑空出現似的,命中注定要讓我帶回家。這部款式略過時的咖啡機,一按開關亮起綠燈,便開始在我的生活裏產生漣漪效應。
每日至少要飲兩杯咖啡的母親曾對我說:「你的血液裏也流着咖啡。」以前我不以為然,覺得自己永無法長成愛吃苦的大人,原來預言總在你未察覺時成真。針頭刺穿膠囊封膜,靜待萃取出來的咖啡濾液從慢到快流下,我的早晨好像從此多了這一分鐘。我徘徊在超市貨架前,逐字細讀每款咖啡膠囊的介紹。到朋友家作客,一邊把玩他們的意大利摩卡壺,一邊取下書架上講咖啡的入門書籍,終於讀懂了 Flat White 與 Latte 的分別,知道原來不同咖啡機器對磨豆的粉末粗細各有要求,以及咖啡豆標榜 Arabica 的意思,並為這種果實短暫的賞味期限嘆息。過往會因攝入咖啡因而出現的心悸,不知何時退別無蹤。
與多年不見友人在下雪天重逢,她提到正準備應徵咖啡店的工作,我厚著臉皮蹦出一句:「那可以嚐一下你沖的咖啡嗎?」她翻出一小包日本咖啡豆,放入磨豆器中旋轉了無數圈,熱水從天鵝頸般細長的壺嘴,均勻地澆在咖啡粉上,像滲進了泥土而變得濕潤,濾液淌滴進玻璃壺裏。這個畫面在哪裏見過呢?在台日合拍的電影《寧靜咖啡館之歌》裏,小女孩走入海邊的小木屋,初次看到手沖咖啡的泡沫微微浮漲,在她這個年紀喝下微苦的飲料仍滿足地捧著馬克杯,相較於貪戀著巧克力之甜的弟弟,她顯然是個不得早熟的孩子。在最近看的日劇《再見的延續》,女主角雖懷念已逝未婚夫,仍不忘如常過活,在早餐前親自沖咖啡,不徐不疾地用熱水在濾壺上劃圈,就好像生活的步調仍在掌握之中。
總覺得手沖咖啡的悠長緩慢,要感受研磨咖啡粉的細度、水溫、速度,從心傳遞到手上,與日本追求極致的匠人精神相當契合,溫熱的香氣含蓄繚繞,也投映了日本人那份專注而寧靜的氣質。咖啡在這兩套作品都有著重要戲份,更以相同的鳥瞰角度,拍下咖啡豆在烘炒過程中翻旋,還有流水澆落咖啡粉的圓圈,讓我想起了另一法國新浪潮經典 ── 導演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在《我所知她的二三事》(Two or Three Things I Know About Her)俯拍一杯攪拌中的咖啡,畫外音說著抽象的哲學思想,濃黑的液體與時聚時散的氣泡,在這種近距離之中,你已辨不清杯裏是咖啡漩渦還是宇宙的星塵。拉遠仍是一片平靜,但注視這深邃的啡色汪洋,卻看到生命像一點點泡沫形成又消失的洶湧。
這個充滿禪意的「一啡一世界」鏡頭,需要太多深沉的思考空間,不易入口。手邊是剛好喝完的開心果咖啡,突然記起今年的 PANTONE 流行色「摩卡慕斯」(Mocha Mousse),如若口感疏鬆綿密的雪芳蛋糕,擺脫了巧克力的稚氣甜膩,又未至於黑咖啡那麼苦澀,是成長的中間點,似乎也很適合將迎來 29 歲的我,沒有準備好做 100% 大人的心境。《寧靜咖啡館之歌》的咖啡師說,某顆咖啡豆可能被園中的大象踩過,因此手中捧著這罐豆,是另一個世界來到你眼前。將咖啡機放到街上的那人,大抵不知道,我的世界因他拓闊了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