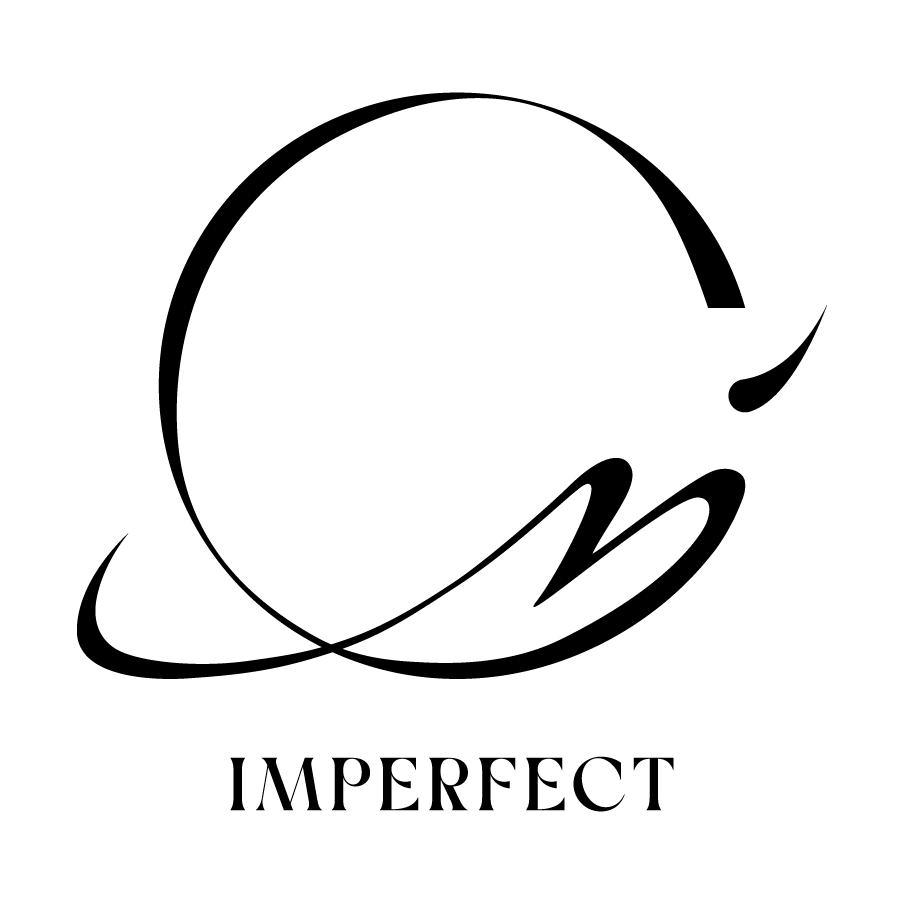致 不夠慘烈卻持續失血的日常:Sasha Alex Sloan,厭世代的集體止痛貼
我想每個人都有來自原生家庭的課題需要面對,記得第一次聽 〈Older〉 時的那份觸動難以言明,那些積累而來的惱怒與委屈,就在那 3 分 09 秒中被溫柔撫平。想起最近在追看的韓劇《苦盡柑來遇見你》,一方面受夠了諧音,另一方面卻又被劇情感動得抹了好幾次眼淚。對啊,也許我們都忘了,自己眼中那難以理解和相處的父母,曾經也是眼眸裡有光的少年。以音樂為刃,剝開成長的痂,將血淋淋的創傷與焦慮,通通封存進三分鐘的旋律結界 ── 這便是 Sasha Alex Sloan 的創作日常。
“ My parents aren’t heroes, they’re just like me
And loving is hard, it don’t always work
You just try your best not to get hurt
我發現父母並不是完美無缺的英雄 他們就和我一樣脆弱
而且相愛很難 愛並不總是管用 ”
── 〈Older〉
深埋在基因裡的詛咒
擁有俄羅斯與愛爾蘭血統的 Sasha,自稱為「永遠的外來者」。父親的酒精成癮像不定時炸彈,母親的憂鬱症則是浸透童年的潮濕霧氣。她在〈Hypochondriac〉唱道:「當我八歲時,媽媽說她想自殺/我卻在擔心明天數學考試」,童稚視角下的家庭裂痕,被譜成近乎殘忍的溫柔搖籃曲。這種「以天真包裝傷痛」的敘事,恰是她對情感勒索的反擊 ── 當世界要求你為他人的情緒黑洞負責,她選擇用旋律築起透明屏障,彷彿在說「我就在這裡,但我不會再承接來自你的詛咒。」
極簡驅魔儀式
不同於當代流行樂的華麗編曲,Sasha 的音樂聽起來總是像被抽乾水分的標本。鋼琴重複著如同催眠般的音階循環,彷彿在模擬抑鬱發作時的大腦迴路,這種「減法美學」在〈House With No Mirrors〉中達到了極致。當她唱著「我想要一間沒有鏡子的房子/這樣就不必看見自己的臉」,極簡配樂反而放大歌詞的窒息感,像用真空袋封存所有自我厭惡的瞬間。
製作人丈夫 King Henry 曾說:「Sasha 的 demo 聽起來就像求救訊號。」但對她而言,創作更像是驅魔儀式 ── 將家族遺傳的負能量轉譯成和弦,最終封印成一張名為《I Blame The World》的鎮魂曲專輯。她在〈Thank God〉中與童年自我對話:「謝謝你沒從屋頂跳下」,字句間閃爍的黑色幽默,是倖存者才懂的破咒密碼。
Z 世代的集體止痛貼
歌迷形容聽她的歌就像「把冰塊敷在看不見的瘀青上」,當「Sad Girl Pop」浪潮席捲全世界,Sasha 的音樂卻拒絕廉價共鳴。她的痛苦從不戲劇化,更像慢性發炎的隱痛:〈Adult〉裡信用卡帳單堆疊的焦慮、〈wish you were here〉中數位時代的情感荒蕪… 這些「不夠慘烈卻持續失血」的日常,精準擊中後疫情世代的生存倦怠。
在去年推出的單曲〈Me Again〉中,Sasha 唱著「我終於認得鏡子裡的人」,電子音效就如解鎖封印的咒語迴響。這或許是她對「情勒封印術」的終極詮釋:當你能將創傷轉化為藝術,那些曾被勒索的情緒,終將成為最鋒利的自我救贖之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