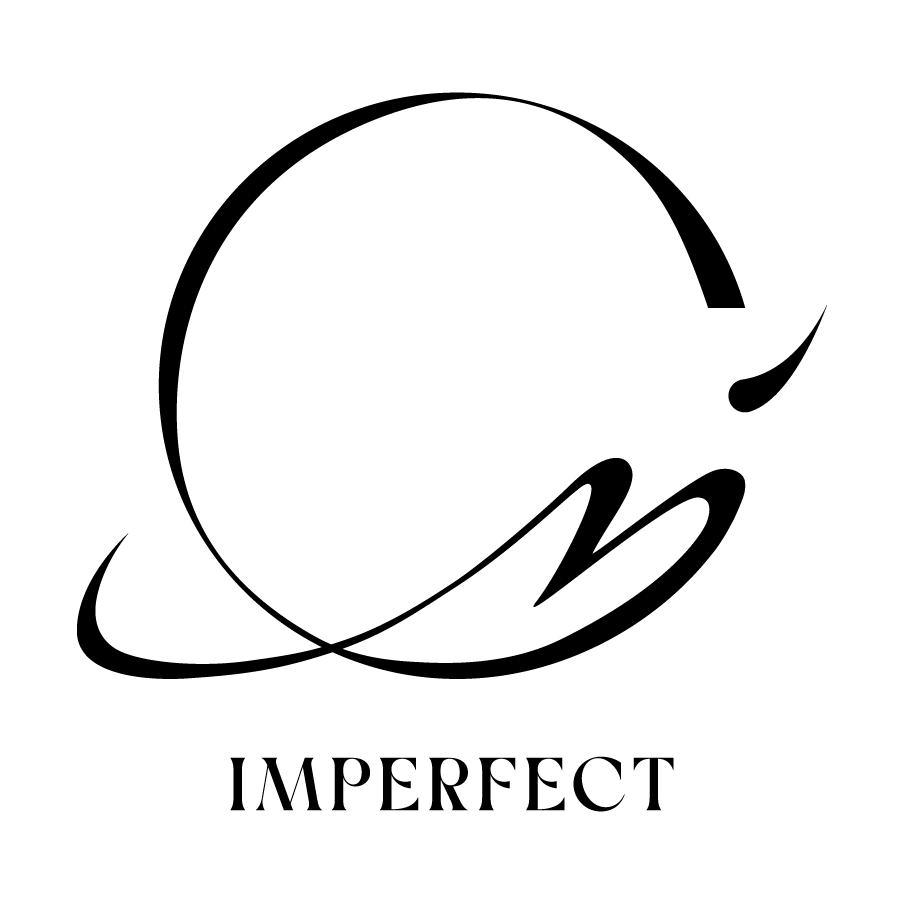夢的作用,是為你排走堆積在心底的情緒垃圾 ── 藍奕邦
上一次和藍奕邦面對面對談,是在他剛宣佈「歸位」,推出〈生〉之後不久。還記得那份歌詞所帶來的撼動,就和當年第一次聽〈六月〉的時候如出一轍。之後他陸續釋出了〈醫生我無病〉、〈竇〉、〈圍牆倒下前〉數首新作,再到上月底剛派台的〈情定唐人街〉,藍奕邦歸位了一段時間,在心境和狀態上都或多或少起了好些轉變,而這次見面,也確實感受得到他逐漸重新適應幕前生活的那種遊刃有餘了。
最難做的一首歌
〈情定唐人街〉的誕生,除了是受到近年選擇移民的好友們的啟發,也源自於他自小對寶島流行曲的情意結。「小時候家裡聽很多國語流行曲,像是姚蘇蓉、尤雅、青山,那些 6、70 年代的舊歌,大部份我都會唱。而我第一個偶像,是鄧麗君小姐。」亦因如此,多年來他的創作都不乏小調這種調性的歌曲,譬如 2004 年劉德華的〈常言道〉,還有近年周國賢的〈守口如瓶〉。到這次的〈情定唐人街〉,他隨即表示這是他多年以來最難做的一首歌。
「對上一首我覺得非常難做的歌是〈晚晚禮拜六〉,因為那時候的轉型是很急劇的,由一個很文青,鋼琴書生的形象,忽然間來個這麼大的反差,那其實是很難拿捏的。」這次的困難之所以更高,是因為〈情定唐人街〉雖是一首很久沒出現的老歌風格作品,卻不能真的把它當成是一首老歌那樣製作。「我不想讓人覺得〈情定唐人街〉是一首致敬作品,或覺得我是嘗試去做 3、40 年前的東西。所以那個拿捏是困難的,無論是怎樣和夕爺溝通,到首歌該怎麼編,MV 要怎麼拍,我想大家都花了很多時間去思考如何呈現出一個『2023 年新歌』的畫面,而不是復古或懷舊。」
除此以外,他笑言還有一個尷尬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年紀。「這首歌如果你給林家謙唱,或者你給 MC 唱,甚至乎給阿 Jer,其實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如果我這個四十幾歲的叔叔,忽然間走出來唱一首這樣的歌,大家可能就會問,你是不是要轉投流行經典五十年的系列?」
於是,他找來了三位電子音樂人 hirsk、Shelf-Index、Voel 來負責編曲,透過這些在成長過程中不曾接觸過國語老歌薰陶的年輕人,為這首歌帶來新穎得來又不失原有風味的面貌。「其實他們剛開始也是一頭霧水,但就是這樣才好,因為當你對這首歌稍為有 reference 的時候呢,就會很容易做回以前那些東西的了。」至於 MV,也找來了新生代導演 Rose 合作,拍出如同周星馳 cos《阿飛正傳》的感覺,充滿幽默感之餘,又有少少神經質,perfect。
娘到盡頭便是潮
他觀察到,近年的潮流就是有很多舊有的東西被活化,而其中一個激發他去做〈情定唐人街〉的原因,是因為串流平台。「我們以前的聽歌模式是買 CD 或 Cassette 帶,但現在的年輕人是很 random 的,random 到一個地步是,可能這一刻在聽 YoungQueenz,下一首可以突然跳去鄧麗君,再下一首到 JB,然後是關淑怡,他們是這樣聽歌的。很簡單,總之覺得好聽,覺得正,自然就會喜歡,已經不會再去分新或舊了。」而這亦是他之所以在 IG 宣傳新歌時加上了「娘到盡頭便是潮」這個 hashtag 的原因,甚麼是「娘」,甚麼是「潮」,各人自有定義,甚至乎,已經不再需要去定義了。
脫節而幸福的生活
剛才亦有提到,〈情定唐人街〉這個題材的靈感是源自於那些近年接連移民的好友們,他早在 11 歲那年便移民加拿大,也曾深深體會過他如今口中那種脫節而幸福的生活。「當年的科技沒那麼發達,聽歌真的是要等 CD 從香港寄過來。生活很簡單,我那時就是上課下課,週末開 45 分鐘車去唐人街,租一堆劇集錄影帶,然後花一個星期看完。」他回憶道。他分享當年有一間很喜歡的書店,會定期上架來自的香港書刊雜誌,雖然價格往往會貴個三倍,但他還是會買,原因無他,就是思鄉,想要知道香港正在發生的事。
自去年 11 月通關,他便飛往倫敦和台北探望移了民的朋友們,發現科技雖然變得發達了,但移民的生活模式卻仍然和當年很相似。「因為離開了香港,總會有點所謂的 home sick,他們真的會花很多時間去找香港食物,甚至他們原本都不太看香港的娛樂節目,但去到外國反而看了個遍。」他說,移民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它可能會將你的生活模式徹底改變,而看著這種轉變是很有趣的。「所謂人離鄉賤,物離鄉貴,一罐豆豉鯪魚,在唐人街見到你是會當寶的。所以我覺得,怎樣都好,我以為自己沒有所謂的鄉愁,但每當去到一個新的地方居住,才發現自己還是抹不走香港那滴血,而唐人街就提醒了我,其實我是一個需要接觸到香港事物的香港人。」
歸位之後
自「藍奕邦歸位」已有一段時日,回想著成為獨立音樂人的這段日子,他笑說有時會覺得有點太過自由了,自由得叫他無所適從。「我跟 Kendy Suen 討論過這件事,就在我們各自離開舊公司,成為獨立音樂人的時候,我們發現自己好像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她是這樣形容的,那就像你被綁架了,被關在地牢,直至很多年後,你突然成功逃走了,再次見到太陽,你卻覺得好刺眼,甚至有點想重新躲回洞穴裡。」從〈生〉到〈醫生我無病〉的那段期間,他正正就是有一點這樣的感覺。
「十幾年在大唱片公司的制度下成長,忽然間對我說我可以有自主權,可以自行決定往後的路該怎麼走的時候,你反而會覺得有點不習慣。」直至完成〈竇〉,他才越來越懂得去享受現在那種只需要向自己交代的自由自在,也能夠更為自在且做自己地面對傳媒和觀眾。「我出道的那個年代,歌手是一定要有偶像包袱的,縱然我當年非常抗拒,但在潛移默化之下,你還是會覺得『我需要有』,因為那樣才生存到。」至於如何拋開偶包,他就表示那需要時間,但一旦學會,就能找到一個很舒適的狀態。當然,他還是會保留一點點必要的偶包,所指的是該打扮的時候還是要好好打扮,而不是蓬頭垢面地出現在人前。
Social Media Detox
今時今日,不單是藝人,對於年輕一代來說,好像總有種無形的壓力,就是只要不活躍於社交媒體,你這個人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你的 IG 帳號,就仿彿就等於你的 idenity。「別人怎麼認識你、看待你,都是透過 IG,我覺得這是有點 mess up 的。我認識你是想認識你真人,而不是你的照片。」前陣子仍在未開始新歌宣傳的「休漁期」,他進行了一次 Social Media Detox,unfollow 了所有人,也不玩 IG。他發現,平日接收到的資訊量太大,而其實大多數人在做些甚麼,其實和自己完全無關。「近來有慢慢 follow 返人,因為我出歌(笑)。但我的確覺得,間中讓自己清空一下,不讓自己接受太多資訊,其實是健康的。」
做夢是一種排毒
除了透過遠離社交媒體為心靈排毒,他認為其實做夢也算是排毒的一種。「夢其實是為你排走一些堆積在心底的情緒垃圾。前陣子我看了一齣戲,叫做《Beau Is Afraid》(寶驚魂),其實它就是一個整整三小時的惡夢。但我亦會想,有時發一些很地獄的夢,某程度上其實也是在幫你紓壓。」說到近期印象最深刻的夢境,他表示是發生在生日前夕那段心情低落的日子,其實他已經不大記得夢的細節,但那份釋懷的感覺,至今讓他覺得溫暖。「我記得我在前一晚許了一個願望,希望能有一個釋懷,然後,那個晚上我就夢見我的媽媽和婆婆。隔天一醒呢,整個枕頭都是濕的,我知道自己哭過了,而胸口那份沉重亦隨之消失。」他覺得自己其實並不需要記得夢裡究竟發生過甚麼事,因為那感覺就像是媽媽和婆婆聽到了他的請求,所以透過夢境幫了他一把,讓他好好哭出來,再舒舒服服的過生日。「我不是一個容易哭的人,有時就算我覺得需要哭,也是哭不出來的。所以,多謝她們幫我把那團鬱氣吐了出來。」
他說自己還有一整個系列的惡夢是關於演唱會的,每隔一至兩個月就會出現一次,每次的場景都一樣,就是他忽然被告知自己要上台唱歌,卻完全沒有採排過,對於要唱甚麼歌也毫無頭緒,但已經被推了上台,上到台還發現自己沒穿褲子之類。「有個更恐怖,就是我夢見在演唱會後台忽然有人對我說『阿邦,我哋冇幫你 book 化妝啊,我叫你印傭姐姐幫你化啊。』,我就『吓?』(笑)。」演唱會系列的惡夢驚嚇得來總又帶點詼諧,但他深知這些夢境其實都指向了一個他一直以來的結。「其實這麼多年來,每次要我站到台上唱歌,我都是有壓力的,會很擔心自己 deliver 得不好。不過多得這些夢,起碼讓我在起來時笑一笑,知道這些事情在現實生活根本不會發生。」
最後我問,假如能夠自由選擇今晚的夢境,他最想看見甚麼樣的景象?他想了想後大笑著表示:「…春夢(笑)。京華春夢,不是(笑)。」回到認真 mode,他說自己其實曾有好幾年的時間,每一晚都會發惡夢。「最恐怖的是,你會夢到一些現實中正在發生的事,但那些事情全部都出錯。這才是最讓人害怕的夢,因為醒來後你會分不清夢和現實。」所以,現在的他覺得除非是很好的夢,否則最理想的就是甚麼夢也不要發,一覺睡天光,如此便好。
情像酒家靠仿舊馳名
人像新聞有幾多長青
惟願我們名字像對春聯
對得久遠便相稱〈情定唐人街〉
photograph by Sam Tso, assisted by Tim Chan
make-up & hair by Kaho Cheng
produced by Ruby Leung
venue 九龍城同撈同煲火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