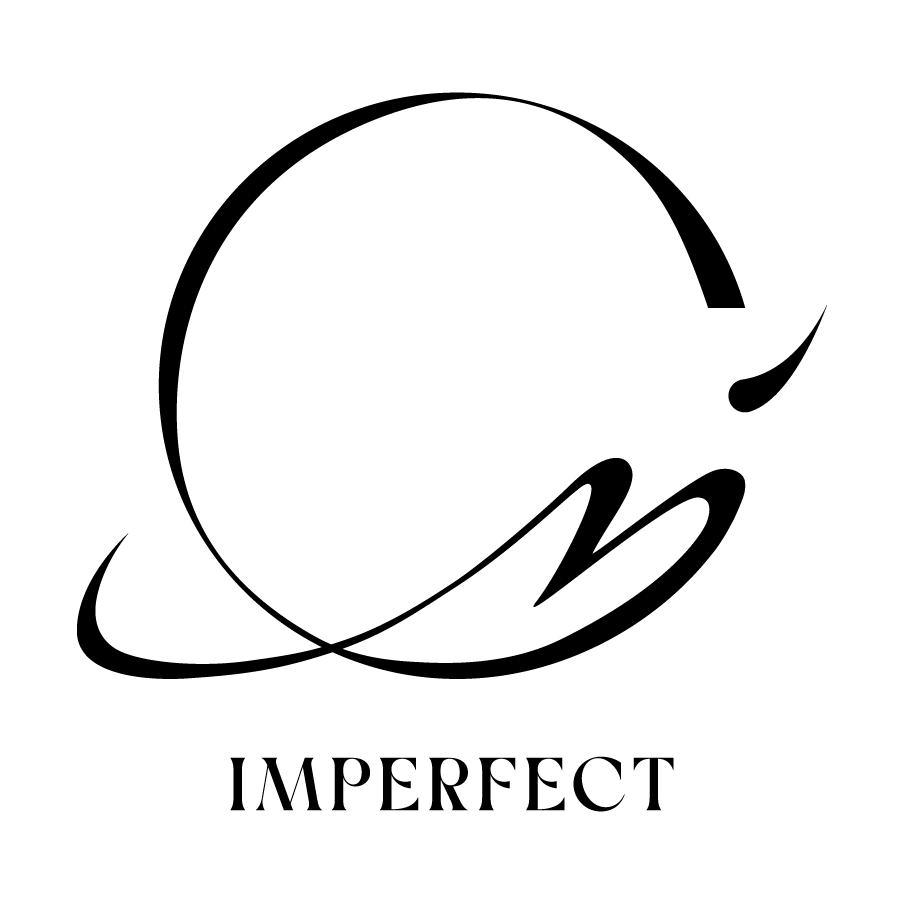「我去過一次摩洛哥,差點死在那裡。」:Queer 、紋身師、旅居者的遊牧人生 ── Benjamin Au
編輯的工作轉眼便踏入第七個年頭,雖然曾無數次卡在瓶頸處動彈不得,也曾狠狠撞過無次數牆,猶幸過程裡還有大大小小的快樂中和了上述苦與難,讓我至今仍然享受去當那個聽故事的人。這些年來聽過寫過許多人的故事,起初我並沒有注意到,原來每一場對話都會流入生命成為養份,每當遇上人生的坎,儲存在記憶庫中的某句話就會突然浮現,輕輕扶我一把。
「相信你在做的事,對自己誠實,就能夠打破壁壘。」有些相遇說來也是神奇,去年底透過曾數次鼓勵我要去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的紋身師好友認識了 Benjamin(又稱 Benji,或者 Bubu),而他竟又不約而同地在訪談中說了同樣的話,我想,這大概也是某種來自宇宙的 sign 吧。
旅居人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jamin,我是一個 Queer Tattoo Artist,是在西班牙住了十年的香港人,也是紋身店 MUSEO 的主理人。」時序回到去年十一月,得知 Benji 那陣子剛好回到了香港(他每年春、秋都會回來待一至兩個月,見見朋友和工作),然後我們幸運地約到他離開前剩下的唯一空檔。那天我們相約在他工作的地方,在我快要抵達的時候,突然有個高大的身影在旁邊匆匆走過,雖然素未謀面,但那亮眼的打扮讓我光憑背影便認出了他,而他在我喚了一聲 ”Benjamin!” 之後轉過頭來,露出了燦笑。
聽這個人說話著實太有趣,聊著聊著,他不忘提醒我要是發現他把話題扯得太遠就把他拉回來,我說沒關係,就一起走得遠遠的吧(放飛自我式訪談就此展開)。身為一位旅居紋身師,他每個月都會飛去一個國家工作,目前的清單上共有六個地方,分別是香港、巴塞隆拿、巴黎、倫敦、蘇黎世和阿姆斯特丹,每個地方去兩次,十二個月就這樣過去了。
「歐洲的生活是慢活,可以很放鬆,放慢節奏,看山看海,退休般的感覺。而香港對我來說是一個充電的地方,在繁忙的都市裡聽到電車聲,聽到人們走路和說話的聲音,聽到廣東話,就能給予我很多能量和靈感,讓我感到很快樂。」和許多人相反,他屬於那種需要在城市裡充電,然後去大自然放電的人。「身處大自然的時候,我總會想『我做什麼好呢?』、『下一步做什麼好呢?』、『我該怎麼辦呢?』,對著山和海,反而會令到我有這樣一種緊張的感覺。」再加上,在人煙稀少的郊野,即使精心打扮亦無人欣賞,畢竟路過的那頭大象也不會讚你漂亮,反讓他缺少了一些動力。
「我的人生就是不斷去做這三件事:尋找 Comfort Zone、建立 Comfort Zone、離開 Comfort Zone。所以我每隔五年就會轉移據點,先是德國,然後是西班牙,接下來就是泰國。」他說,每座城市都有其獨特的地方,人們想要的東西都不盡相同。每一次離開,他都帶著許多經驗值前往下一個目的地重新開始,而語言就是其中一環。「學了第三個語言之後,當你學第四個語言就會覺得得心應手了。」他相信若要真正進入當地人的生活,就一定要學會講當地的語言。不過語言這回事,只要荒廢一段時間就會變得生疏,像廣東話,他就對許多這幾年才出現的新興詞彙表示不解,會一臉疑惑地問:「嗯?甚麼是『蛋蛋後』?」。
命定之途
講到當初之所以成為紋身師的契機,他就表示其實是源於對畫畫的熱愛。他從小就喜歡畫畫,六歲那年,坐在旁邊的同學叫他畫一架飛機,畫好之後對方竟塞了一張百元鈔票給他。他開心地衝回家跟母親說自己賺到了人生第一張鈔票,說自己將來一定要做藝術家,他覺得這就是自己的命定職業。母親聞言先說了句:「嗯,厲害。」,然後不忘向他拋出問題 ──「你知道藝術家是怎麼賺錢的嗎?」,他回答:「畫畫吧。」,母親淡然地回道:「嗯,也對,但你要在死了之後才會有錢。」。六歲的弱小心靈在當下晴天霹靂,但母親心裡明白,孩子已找到屬於自己的道路。「我媽媽是一個生意人,先把現實攤在你眼前,但另一方面,她又會不斷用行動去支持和栽培我,例如她從來都不帶我玩具店,而是去文具店看筆和紙,所以我真的很感謝她。」
就這樣,他在中學畢業後便進了設計學院,及後再去德國深造。前後讀了十年的藝術和設計,也就是人們口中的學院派,一筆一劃,都是歲月練就出來的扎實功架。至於為甚麼會選擇德國,是因為他想要挑戰自己。「我想找一個我不會當地語言,一個朋友都沒有的地方,於是我就 air drop 了自己去那邊,一個人重新開始,start from zero。」從語言開始,每天讀德文,再慢慢認識朋友,逐漸建立一些東西。儘管剛開始的生活無比艱難,但他的心和眼界亦由此打開,抵達更廣更闊的世界。
深造期間,由於有許多空餘時間,於是他開始在 YouTube 自學紋身。「我的師傅就是 YouTube,它教會了我所有事。但我絕對不贊成大家這樣做,因為實在太多冤枉路要走了。」開始以紋身作為事業以後,他花了很多時間去建立自己的品牌。作為一個身處異鄉的香港人,一切雖不容易,沿路卻讓他看遍了各式獨特的人生風景。那個自六歲起便一直在問自己「我能不能以畫畫為生?」的小男孩,如今已成長為一個對自己的信念堅定不移的藝術家(p.s.在生時就能賺到錢養活自己那種)。
靈魂之間的相互吸引
在柏林以紋身師的身份起家,但他的紋身店 MUSEO 卻選址巴塞隆拿,其原因是出於愛情。他的前女友是西班牙人,也是一名 Bisexual 的 Queer。「我們在柏林認識,她有趣的靈魂吸引了我,我們在一起六年,在疫情來襲前搬了去巴塞。在這段關係裡,她給予我很多空間,還有令我真真正正去思考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令到我去問自己『究竟這個是不是我呢?』。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折點,也從而令我發掘了一個嶄新的我。」
他就像電影《Danish Girl》的主角 Einar(Lili)那樣,從「一個佬」搖身一變成為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自己。「是她給了我第一條裙,一穿上去,我就有種 “Bling!” 的感覺。然後她幫我化妝,成為我轉型的開始。現在的我以 Non-binary 的方式去生存,穿自己喜歡的衣服,對自己誠實。」他說「誠實」是很關鍵的一點,像他就常跟自己說要多吃點「誠實豆沙包」,吃完之後向鏡子發問,映照其中的那個人,自己是否喜歡?
他形容和前女友之間的相處模式也很有趣,對方會擔當比較男性化的一方,而他則是比較女性化的一方。「調轉角色之後,我才發現我以前認為男生一定要做的那些任務和職責,原來都是一種性別定型。」同時間,他亦發現原來做女人真的很難。「原來穿高跟鞋是要走慢一點,才想起我以前都走得很快,沒有顧及到女朋友的感受;原來吹頭就是要吹半個小時,但以前我總覺得為什麼對方要搞那麼久才能出門。」親身體驗過作為一名女性的日常生活之後,他說自己現在終於是用兩種性別去體驗這個世界,也才發現,原來自己之前看到的世界只有一半。
生命影響生命
「我很喜歡踩界,喜歡測試社會的底線。二元的世界就是喜歡將所有事情分成兩邊,但其實有很多人是遊走於中間,像是性別。」轉型以來,他對於旁人的目光早已習以為常,像「噢,這個男人來的。」或者 “This is a guy, look at that.” 之類的說話也是一直不絕於耳。「當他們在想我究竟是男生還是女生,0.5 秒之間,就將我放進了一個盒裏面。而 Non-binary 就是,我有時可以是男生,有時可以是女生,視乎心情而定,沒必要將男和女的定義框得太準確。」
在歐洲語言裡面,很多都會有陽性或陰性名詞之分,但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對第三性以及無性別主義的認識和重視,近幾年也出現了一些中性的字彙,例如在西班牙語中,”Guapa”是代表「靚女」,”Guapo”代表「靚仔」,而 “Guapi“ 則是男女共用的「靚人」之意。「像現在我去買咖啡,咖啡師跟我打招呼的時候會說 “Hola Guapi!”,開始越來越多人這樣說。其實很有趣,原來文字是會不斷轉變的。」
除了受到讚賞或支持以外,還有一個讓他繼續堅定地做自己的理由,就是他發現原來這樣的自己能夠影響到別人的生命。「有一次在西班牙,我以一個很華麗的女生造型走在街上,回家後收到一個 DM,對方表示在街上踫到我,覺得很漂亮,亦因為如此,他決定去做一件事,就是回家將偷偷藏在衣櫃底的箱子,那個裡面放滿裙子的箱取出來。」對方向他表示,之所以一直不敢拿出來,是因為自己有太太,還有兩個孩子。直至看見他穿得美美地笑著走在路上,才得到了向太太坦白的勇氣。「如果有人因為我而改變了他的生命,我就已經覺得很開心,所以就算有多少衝過來用髒話罵我的人,我也不介意。能夠影響到一個人的生命,就已經很足夠了。」
強大心臟之養成
他說,強大的心臟是鍛煉出來的。「被讚賞和被攻擊,一個給予你自信,一個告訴你現實。但你只要相信你自己,相信你在做的事,對自己誠實,就能夠打破壁壘。」他每次開 IG 的 Q&A,都有人會問:「究竟怎樣才能像你一樣成為一個閃亮的自己?」,而其實從前的他,也曾是一個沒有自信的人。被香港社會那「男生就要練大隻,瘦得像排骨那樣就不合口味」的框架所定型,迫自己去健身,喝大隻奶粉,吃很多碗飯,吃到想吐還是無法達到人們眼中那所謂的標準。「可能是我用的方法不對,又或者很大機會是我心裡面根本不想成為那個人,所以我的身體很誠實地告訴我,你就算給我多少澱粉質,我都會踢出去。」然後故事就回到他遇上前女友,對方給予他了許多的支援,告訴他往後的路該怎麼走,也才有了如今的他。
「原來在這個世界裡,你只要成為小眾,你就要去勇敢,你必須強大,必須隨時準備去抗衡這個世界。」他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人都會讚賞他很勇敢地做自己,開心之餘,他也不其然去思考,為什麼做自己要勇敢?「就是為什麼我穿自己想穿的衣服要勇敢呢?我以前是個直男,為甚麼沒有人跟我說『你喜歡女生很勇敢啊』的呢?」
面對人類的氣力
每一天,他在起床化好妝後,都會看著衣櫃思考一個問題 ──「我今天究竟有沒有力氣面對人類?」,要是有的話,就穿得華麗一點;如果覺得有點累,狀態不好的話,就穿得輕鬆一些。「有過很多衝過來罵我的人,說甚麼男扮女裝,或者香港不歡迎你,叫我快點走之類。又例如去韓國旅行,我頭兩天是穿短褲,後來真的穿回長褲算了,免得太多人衝過來罵我 “shibal”,就算年輕一輩的人都會不理我。」甚至乎,他還試過被偷拍。「有天穿得比較短,我在地鐵站走上樓梯的時候,感覺到後面有陣風,回頭就看到一個鏡頭在下方。」他當下立刻轉過來頭「喂」了一聲,而對方在驚嚇地說了一句「男人來的」後便落荒而逃了。
瀕臨死亡的邊緣
他說,世界太大了,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文化,你無法爭辯,也不能罵人,就只能去尊重和適應。「我去過一次摩洛哥,那是個穆斯林國家,我差點就死在那裡。」事情發生在五年前,他和前女友去摩洛哥玩五天,期間一直很遵守當地的傳統,當地人也並沒用特別的眼光看待他,直至最後一晚。「那天她胃痛留在酒店休息,我就出去市集買菜,去到後突然有人從後推撞我,抓住我的手,問 “Are you gay?”。」他想起自己忘記卸下紅色指甲和脫下大耳環,加上另一半不在身邊,短短的十秒間,已經有十個以上的壯漢衝過去拉扯和推撞他,不斷重複著同樣的問題。
「我那時很害怕,覺得自己會死在那裡,但這種時候人的大腦會轉得很快很快,我那時在思考紅色指甲油該怎麼解釋呢,最後就說了 “I am from Hong Kong. Do you remember, the flag of Hong Kong, the color.”,我說紅色是我們的 lucky color,每個男人結婚都會擦上紅色指甲油去 honeymoon,但我老婆今天不舒服在酒店休息。」而他當時手中剛好戴了幾隻戒指,拿著剛買的兩碗麵,對方才終於冷靜下來,對他說 “Oh you are married. You are not gay.”。「他們說這裡不可以這樣,他們可以打死我,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害怕。」最終壯漢們就這樣友善地放走了眼前這個結了婚的直男。
後記
完成在工作室的拍攝之後,我們去到大坑拍一些外景鏡頭,途中剛好遇上一群頭戴紅色 cap 帽的旅行團,加上引來許多好奇目光和慈祥姨母笑的 Benjamin,整個畫面看起來極有趣。
「我經常有一句話就是,今天的笑容來自昨天的眼淚。我覺得今天這個開心的自己,是要經歷過低谷,你受過打擊,哭過,不開心過,才會感覺到自己存在。」他續說,唯有離開舒適圈,才能找到如今的快樂;而對於現在的快樂也不要自滿,繼續保持好奇,多看看這個世界,成就更為強大的自己。
featuring Benjamin Au
photo by Sam Tso, Benjamin Au
video by Henry Yeung, assisted by Marco Tam
video edit by Henry Yeung
interview by Jay Chow
produced by Ruby Le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