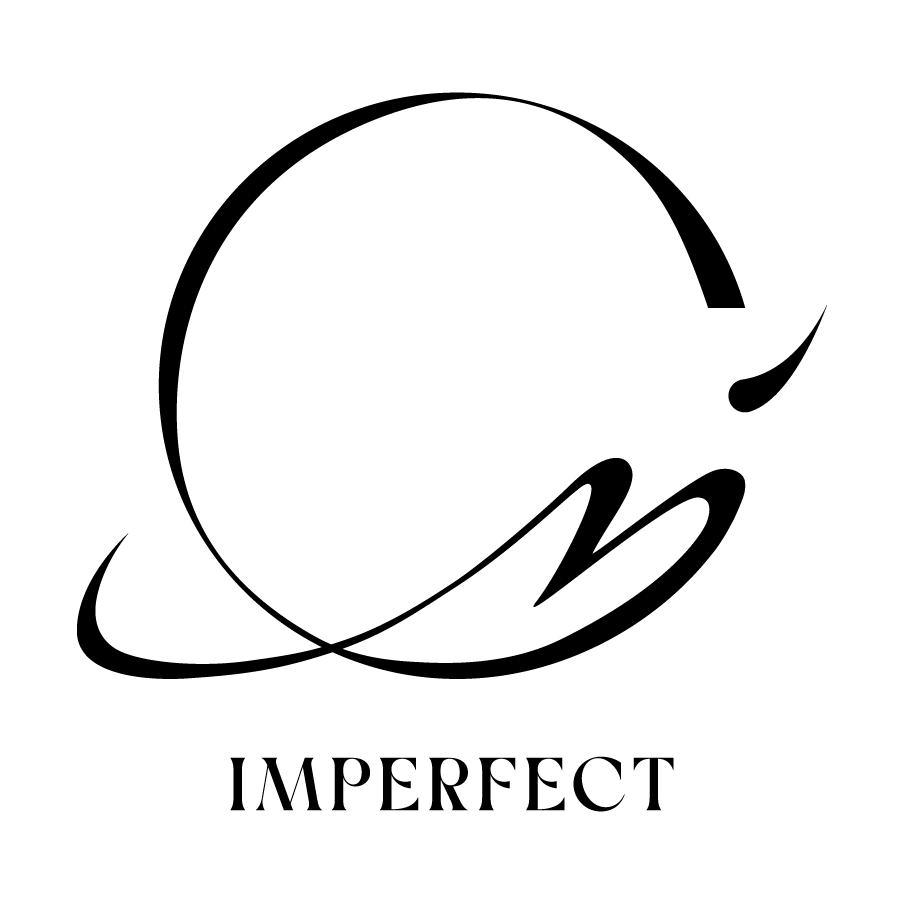最孤獨的時代,我們如何才能真正被理解? ── 多媒體劇場《獨奏曲》
孤獨之於我,是一種情感回應,是無所適從,卻也是日常。每當我們想和誰產生連結卻無法被理解或滿足,孤獨便隨之成形,滲透我們,蠶食我們。在這個號稱最孤獨的時代,我們如何才能真正被理解?
多媒體劇場《獨奏曲》的兩位主創藝術家兼導演趙朗天(Alain)和吳子昆(阿昆),近日便以「孤獨」為題,聯同兩位出演者徐曉晴(Ashley)和馮晟睎(Nelson),在劇場建構一個半私密半開放的房間,和觀眾一同拆解孤寂。有趣的是,在接到這次採訪邀約之際,我手頭在讀的書剛好就是 Lars Svendsen 的《孤獨的哲學》,而今期的主題又是「脆弱的房間」,種種不約而同,讓我不禁思考起宇宙這次想要傳達給我的訊息,可能是「多出門見見人」,又或許只是「別想那麼多,趕快工作」。
拆解孤獨
之所以會選擇以「孤獨」作為《獨奏曲》的主題,是因為兩位導演都認為這是一個儘管很貼身,卻也沒甚麼機會直接拿出來面對或討論的事情。「孤獨這個詞是新的,在工業革命時期才出現 Loneliness 這個字;而 Solitude(獨處)則一直都有。不知道是不是疫情的關係,人們獨處的時間變多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契機去重新認識自己。」Alain 如此表示。
(左)徐曉晴Ashley(右)趙朗天Alain(上)馮晟睎Nelson(下)吳子昆
至於選用《夜曲》的原因,他便談及這首曲對他青少年時期的影響。「我是獨生子,十多歲的時候,不開心就會聽蕭邦,慢慢發現,雖然它很接近我的情感,但不是我的情感,所以它驅使我去學作曲,寫一首屬於自己的音樂。」因此,《夜曲》對他來說也是一種溝通的狀態。我們永遠都無法完整地表達出所有的情感,但能努力去嘗試和理解,容許自己可能會有一百種面向;容許自己有時是好人,有時是壞人;時而狂放,時而孤獨 。
各式各樣的孤獨
正如人的複雜性,孤獨的形態亦非單一的,它擁有著各式截然不同的模樣。對 Ashley 來說,最容易感到孤獨的時候與獨處無關,而是當自己身處一個明明很多人,卻感覺自己格格不入的場合的時候,那種被孤立的感覺反而來得更加深刻。而 Alain 的孤獨,則來自於想像和現實的落差。「譬如當你跟一個很熟悉的人共處,卻突然間感覺到陌生,或者溝通不良,那個轉折是令我覺得最孤獨的。」法文有個詞叫 Jamais vu,可說是 Déjà vu(既視感)的反面現象,意思是一些你每天都會看到的東西,突然有天就覺得陌生了,然後發現原來你一直只是投射了自己的幻想在對方身上。
阿昆甚至曾試過接到一個疑似詐騙的陌生電話,是一位婆婆打來的,聊著聊著,最後發現對方其實只是亂打電話,想找人聊聊天。「我本來在等她甚麼時候露出馬腳,誰知是真的。我就想,到底是處於甚麼樣的狀態,才會去到要亂打電話找人聊天的地步呢?」
孤獨本無害
絕大多數時候,當我們說出一個形容詞,便會自動為其賦予了某種帶有情緒的定義,褒或貶,正面或負面。但 Nelson 認為,孤獨一詞對他來說是中性的,是一種狀態,並沒有好壞之分。「孤獨就和脆弱一樣,給人感覺好像很負面,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我是一個都很習慣獨處的人,本身是自由工作者,而且住得很遠,平常會獨自去晨跑,當下整個世界就只剩下我的呼吸、節奏、步伐,我覺得那個時候是最孤獨的,但不是甚麼壞事。」他緩緩道出自己對孤獨的解讀。對此,同樣享受獨處時間的阿昆亦表示認同。「孤獨是一面鏡子,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自省的機會。」孤獨本無害,有害的只是後來我們因不安而加諸的種種意念。
孤獨流行病
這個年頭,不止思念是一種病,孤獨也是一種病。不少研究都曾指出孤獨已成為一種當代流行病,也就是「孤獨流行病」(loneliness epidemic),更有說孤獨甚或會增加死亡風險。對於這種「孤獨致死」的論調,他們又怎麼看?
「對於孤獨是一種病的說法,我覺得也是的,而且是具有傳染性的那種。」阿昆表示。「與其說是孤獨致死,不如說是因為極度且持續的不開心而死的,也就是所謂的心理影響生理。」Nelson 補充道。獨處總是難以避免的,但對其抗性較低的人來說,自然就成了一道難以應對的困難課題。
孤獨的體現
在社交媒體尋求共鳴和聯繫,也算是一種孤獨的體現,Ashley 對此便深有同感。「我是歌劇演員,會需要經營社交媒體,但有時真的不是那麼真實。人總不會無時無刻都那麼開心,但多數人只願意對外分享開心的一面,把狀態不好的自己隱藏起來,製造假像給人看。」朋友越多、聚會越多,並不代表你就能和別人建立起連結,也不保證你能因而消解寂寞,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坎需要跨越,沒有甚麼好比較的。
「所有的不快樂都是源於期望,或者和溝通有關。有時甚至乎連跟自己溝通也不大暢順,你以為自己是那樣,但某天發現原來不是。」Alain 表示。不過,之所以感到難過,有時候也可能是因為沒有好好梳理積累的情緒,就像久未執拾過的衣櫃,回過神來裡面早已亂成一團,想找件外套也不知該從何入手。
消除孤獨
《孤獨的哲學》中有提到:「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孤獨傾向,但我們可以採取各種方式來克服這個傾向。」Nelson 就分享,他有一個開心歌 playlist。「以前全職工作的時候,每當星期五下班回到房間,我一定會播 The Cure的 Friday I Am In Love,自己一個在房間跳舞。」除此以外,他亦喜歡看海,將大海當成情緒的載體,包容一切,帶走一切,人自然就會平靜許多。「找到能讓你感到平靜的方式,可能是大自然,可能是音樂,可能是信仰,一定有東西可以幫到你。」
阿昆認為享受和難以忍受有時候只是一念之差,他亦明白當一個人跌到某個位置,是真的會上不來的。「我有幽閉恐懼症,但在某個情況下才會發生,發生的時候你會無法控制自己,儘管你明知其實很小事,根本不需要那麼害怕。」因此他平常也會做一些正念練習,嘗試減低不可控的情況發生。而 Alain 則是不希望消除心中的那份孤獨,因為對創作者來說,那也是一種原動力,將種種化成作品,就是最好的療癒。
關於《獨奏曲》
身處現今超連結的世界中,人們往往渴望親密與聯繫,試圖在藝術、音樂和文學中尋求慰藉。然而,我們所表達的即使多麼坦露,卻永遠有所隱藏。這種從孤獨中流露自我表達的欲望,在蕭邦筆下化成一首又一首夜曲。
趙朗天與吳子昆創作的視聽演出《獨奏曲》試圖開闢一個空間,讓藝術家與觀眾一同經驗種種難以言喻的情感。在這趟往內探索的旅程,我們會發現,真正把人心連繫起來的東西其實溢於言表,藏於內在世界的呼應與共鳴,既幽微私密,同時卻渴望主體間相互理解。而《獨奏曲》正是在追尋群體連結中保留自我流動時,徘徊於孤獨和獨處之間的一瞬。
作品並非單純的音樂會,而是透過不同調度、分拆、重組音符,就好像是群體、個體、再組合成新群體的過程,發掘全新面貌和質感展現孤獨的思考。
日期:27-29.12.2024 (7:30pm);28-29.12.2024 (3pm)
地點:葵青劇院 黑盒劇場
票價:$280
*現於城市售票網公開發售
photo by Sam Tso
interview by Jay Chow
produced by Ruby Le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