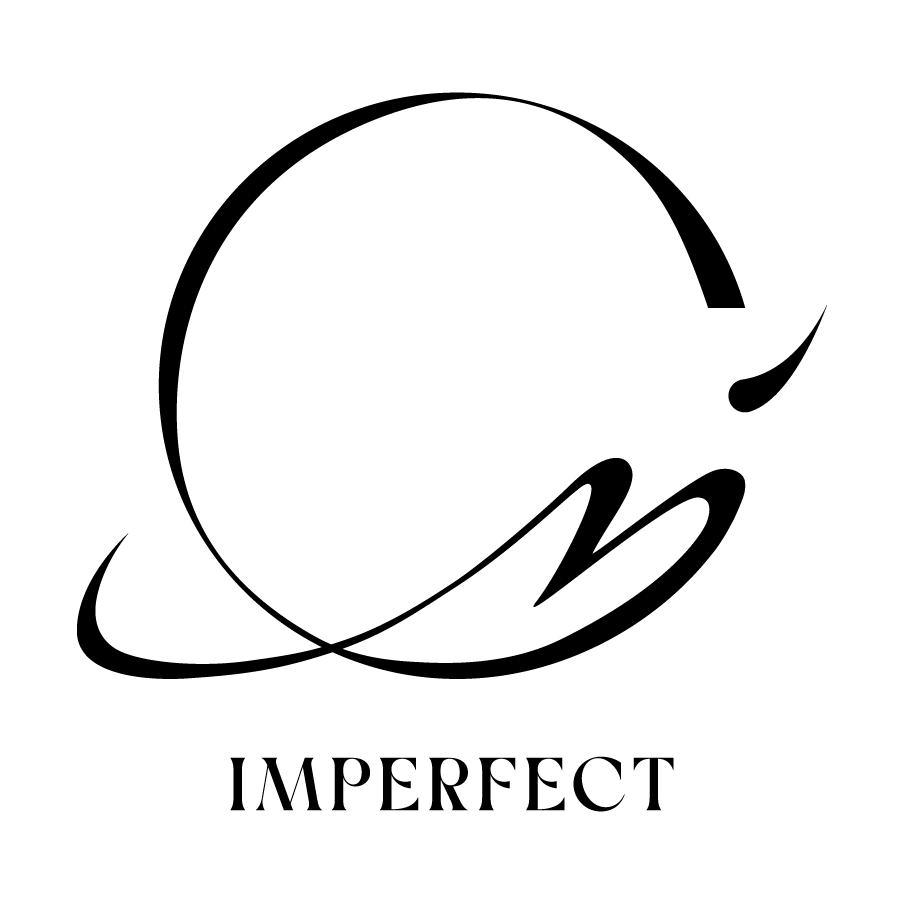「女權」在香港是很敏感的字眼,不在政治上,而是在文化上 ── 紀錄片導演 阮行恩&楊曉芙
以全職創作為職業向來被視為一個極為冒險的選項,在香港尤甚,更別提是關於社會議題方面的工作了。我在某個上午到訪了紀錄片導演阮行恩與楊曉芙(Sharon)那有著擺滿整面牆的書籍的工作室,行恩的知性搭配 Sharon 的活潑,予人的感覺就是一對很合拍的搭檔。和她們聊著以 iPhone 背後的邊緣女工角度去探討現代性別角色、消費主義和移民工人等問題的新作,我也開始對手中握著的那部 iPhone 產生了更多的好奇。
生產線的盡頭
之所以選擇用 VR 去拍攝這次的紀錄片《MADE VR:在生產線的盡頭遇見她》,她們表示二人向來喜歡互動式作品,能夠將觀眾和故事的距離拉近,代入感也會比較高,尤其 VR 就更是能夠讓你 360 度去觀看那個世界。Sharon 苦笑說,製作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其實極多,畢竟 VR 在香港並不普遍,頂多就是用於遊戲或看樓盤而已。因此,作為獨立製片人,要完成一部 VR 紀錄片更是困難重重,資金、技術、資源、人脈都是需要一一解決的問題。
所幸這個企劃最終為努力向外爭取的她們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像是美國 Google 就為提供了最新型號的 VR 相機,後來亦成功打進英國和荷蘭的紀錄片市場。在遊走世界的過程中,她們認識了許多同為獨立製作人的夥伴,互相學習彼此所長,逐漸建立和擴大團隊。
「當你在香港沒人力,沒資源,沒財力,反而嘗試再走出一點,原來就會找到。」Sharon 表示,這也是一種幸運,看似 mission impossible,只要先鼓起勇氣踏出一步(或者很多步),就會發現,可能性其實一直比你想像中的來得更多。
工廠女工的封閉人生
「這是一個極大的群體,亦是一個非常 invisible 的群體。」談到那群在 iPhone 背後默默耕耘的女工,Sharon 表示這對於香港人來說一般比較難想像,因為大部人印象中的女工就是以前製衣業的那些姨姨,但其實她們在中國是一個極大的群體,那老是常出現的 made in China 字樣,背後就是充滿著這些邊緣女性的汗與淚。
「這些女工普遍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十幾個小時不斷重複同一個動作,她們其實也想為自己的人生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但沒有辦法,必須要花那六天去賺錢養家。」接觸過許多女工群體的行恩表示,正因如此,女工們都會很珍惜那只有一天的假期,像是紀錄片中的小五,比起休息,她更想去做義工,或者寫寫文章,來為刻板的生活增添些許色彩。
在富士康近距離觀察過女工們的日常,行恩認為她們最缺的其實並不是錢,而是社會對她們的尊重。「這也是為甚麼我們一直想推動生活工資這件事,就是指在一個正常的工時裡面,賺取足以照顧家人的工資。其實香港也一直有團體在講生活工資,但始終不是一個主流議題。」問題多年來依舊持續,歸根究底是因為這樣的邊緣群體並沒有所謂 bargaining rights,也沒有能夠容納異議聲音的言論空間。
父權社會的無形牢籠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其實男女老少都內化了一個很父權的社會價值觀。」Sharon 表示,譬如紀錄片中的工廠女工小五,她雖然想讀書,卻要為了養家和供弟弟讀書而出去打工。身邊的人只會追問她甚麼時候結婚,生多少個小朋友,但一個連生活都沒有的人,除了自己的家人,還要去 serve 另一個家庭,想到這裡就讓她無比恐懼與絕望。「很多人會將富士康和自殺連結,但其實不止如此。她們的生活除了工作和照顧家人之外甚麼都沒有,她們覺得自己沒有選擇,找不到那麼辛苦的意義是甚麼,也看不到可以有怎樣的變化。」
行恩補充,其實香港亦仍然存在著近似的問題。「香港女性的地位看似很高,但像是 Sharon 剛剛講的照顧者問題,每當家裡有人生病,多數人還是會 expect 女性去做多少少,彷彿是理所當然地要擔負起照顧者的角色。」這讓我想起了《82 年生金智英》裡的一句話:「你知道最讓我難過的是甚麼嗎?醫生反問我,飯是電子鍋煮的,衣服是洗衣機洗的,為什麼我的手腕會痛?」比起身體上的勞累,不被理解和尊重的傷害性其實來得更大。
除此之外,還存在著性暴力和性騷擾的問題。Sharon 表示,許多女工其實是為了避免騷擾,不得已之下才選擇進入工廠。「譬如小五 14 歲出來打工,本來她因為想在靠近家裡的地方工作,於是就在一間餐廳做侍應,但就因為不停被性騷擾,讓她最後寧願入工廠。」
過敏時代
說到在維護弱勢女性權益路上的最大阻礙,就是民間團體的力量終究是有限。「雖然這些往往是關乎整個公民社會的議題,但任何爭取權益的事情,在現在的環境其實都比較難做。」再加上,女性主義/女權等字眼在近年被不斷曲解,有些地方諸如南韓甚至還出現了反女權主義的浪潮,Sharon 對此就表示,其實香港的情況亦沒有好到哪裡去。
「我覺得女權在香港是一個很敏感字眼,不是政治上的敏感,而是文化上的敏感。好像做任何和女性有關的事情都會被人 label 女權二字;好像你一講,對方就會很怕你接下來要說甚麼。」的而且確,有時在網絡上看到那些「女權就是在製造性別對立」、「班女權做咩唔出嚟講嘢」、「被性騷擾是因為你穿得暴露」之類的留言,我也會懷疑自己其實是不是身處於文明社會。
「很多人都誤會了一點,就是女權所講的性別平等,其實不止 fight for 女性的權益,亦是 fight for 男性。譬如男性不需要被定型一定要賺錢多過老婆,或者一定要很陽剛。」行恩補充道。身處這個很多東西都脆弱得彷彿一觸即碎的過敏時代,人與人之間要互相尊重和理解,大概還有相當漫長一段要走。
無力感
Sharon 曾在過去的企劃中引用了一個研究,裡面指出香港除了是「全球生活費最高」的城巿,同時也是全世界最低「生命意義感」的城市,但經過這幾年,她認為情況已經變得不一樣了。「我不覺得一切是了無意義的,若你感受到很重的無力感,其實是源於你很想去做一些事情卻被 push back。這些座城市爆發過許多活力,人們亦找到一些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而現在需要的是沉澱和摸索。在這樣的社會氛圍底下,那些活力和價值該放在哪裡呢?」
同身處這座城市,行恩同意現在一定有很多人都會有種無力感,而我們惟有盡量去思考自己還可以做些甚麼,也只能夠如此。「這次的企劃,我們想表達的就是你作為消費者,其實還有一定的影響力。譬如這幾年很流行的 impossible meat,我看到就連一些茶餐廳或茶樓都有推出,這就是由消費者的意願在不知不覺中推動的事情。」
2022,科技正持續地進步,我們卻和很多東西都 disconnected 了。「採用 VR 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想要將人和生活重新 connect,想觀眾真正去參與這部紀錄片,你要郁,你要做決定,要去選擇,而不止是你看過的無數影片裡的其中之一。」你又是否曾疑惑過,那件正穿著的衣服、剛剛吃過的午餐、手上拿著的東西,到底是怎麼來的?
創作者的生存之道
香港迎來了 97 後的第二個移民潮,曾留學美國的 Sharon 表示,選擇留在香港發展的原因其實很單純,因為這裡是家。「我們是講故事的人,那當然會想講自己屋企,或者自己熟悉的故事。」和行恩在五年前成立創作合作社 Singing Cicadas,就是想有一間專門製作 social justice 故事的製作公司,儘管困難重重,但還是希望能夠繼續走這條路。
二人坦言,作為紀錄片導演,其實很難維生。「我們的生活工資其實都好低(笑)。」Sharon 笑說。「我想這個圈子大家都需要同時做其他工作去維持生計,沒有誰真的可以全職投身在紀錄片的行業。像我就當了全職兩年,但這只是因為我在花著自己的積蓄去做這件事,身邊很多人大概也是這樣。」她們的工作日常,除了專注於創作,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為資助奔波,寫了好幾十個 proposal,飛到世界各地找資源和機會。從香港到美國、英國、法國、荷蘭等地的合作和贊助,全部是由她們親自洽談回來。
行業生態如此,行恩認為倘若要走向更好的未來,除了自己要努力「搵到食」,還要擔起支援其他行家的責任。「不是各自爭餅仔食,而是要一起做大個餅。」當她們發現可以開拓香港以外的可能性來爭取更多資源,將經驗分享給身邊的人,就變成了必須要做的事。
「既然大環境那麼差,那就由我們去製造一個 community 出來,再互相 support。」聽著她們的工作內容和願景,我心想這兩人大概也是處於年終無休的狀態,最後我將這個疑問問出口,Sharon 聞言就笑說:「我是覺得,為了精神健康還是要放假的(笑)。」❂
一部透過身臨其境連繫消費者和工廠工人的 VR 紀錄片,觀眾可做出一系列選擇,並與一位在中國生產蘋果產品的真實工廠女工小五交流對話,故事會根據你的反應進行調整,走向不同的結局。
photo by Sam T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