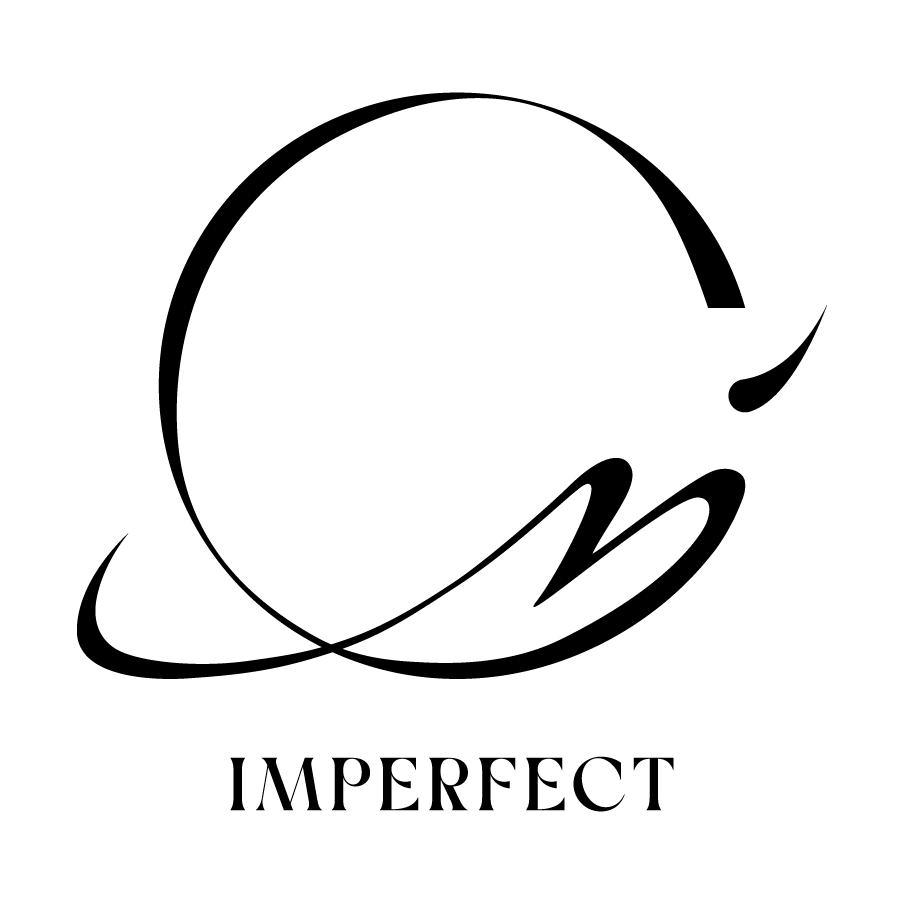「要好好的,抱歉,謝謝。」:草東沒有派對,曾經我們都想要改變世界
自初中被一場演出深深打動,往後的日子裡,除了出國那幾年,我基本上都不會錯過台灣金曲獎的首播。年復一年,早已成為一種習慣,這年的金曲 33 也不例外。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除了黃宣以一票之差擦身歌王,還有盧廣仲在演唱用以緬懷已故音樂人的《為何夢見他》時,出現在大螢幕上的其中一個名字 ── 蔡憶凡。凡凡,草東沒有派對的第二任鼓手,這個笑起來無比溫柔的女生,在去年底為自己二十六年的生命劃上了句號。
戳破糖衣假像
曾經我們都想要改變世界,推翻世間一切的荒誕與不合理,可後來卻還是屢屢被無力感打擊得體無完膚,甚或倒地不起。〈爛泥〉、〈山海〉、〈大風吹〉,這三首歌是我對草東最初的認知,衝擊力確實是強得叫人一聽難忘。
這個年頭,正能量逐漸變成了一種空洞無力的口號式呼喊,不單毫無作為,甚至能讓本已深陷漩渦的人更覺孤單。不少創作者早已察覺到這一點,意會到這個時代的年輕人真正需要的是理解和陪伴,情願坦蕩蕩地脆弱,也不要虛假的堅強。草東之所以能如同藥引般引爆世代的強烈共鳴,正正就是因為他們選擇戳破糖衣的假像,唱出了時代下的種種挫敗與無力,映照了這一代人的陰鬱群像。
他們扔了你的世界 去成為更好的人類
那廉價的眼淚就別掛在嘴邊
什麼也沒改變 什麼也不改變
請別舉起手槍 這裏沒有反抗的人
不用再圍牆 這裏沒有反抗的人〈勇敢的人〉
他們的創作總是以直白且強烈的情緒來貫穿與填滿,憤怒、無奈、恐懼、頹廢、不屑… 將那種彷彿永遠都無法找到出路的絕望感,用盡全力去控訴,而這對於習慣在壓抑的社會之下成長的人來說,既是一記重拳,也是一帖猛藥。
拉回到現實層面來看,聽眾所感受到的強烈共鳴,其實也來自人們口中的「崩世代」(一般指 1990 年後出生的人)正共同面對的種種難題,諸如持續擴大的貧富差距、低薪、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失業、高房價等等,正因無力靠一己之力扭轉困局,才會覺得自己很廢,繼而陷入惡性的情緒循環裡。
我想要說的 前人們都說過了
我想要做的 有錢人都做過了
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們虛構的〈爛泥〉
有血有肉的生命風景
草東唱出了在資本社會所堆砌出的瓊樓玉宇背後的生命風景,字字鏗鏘,有血有肉。但要說是厭世嗎,我認為還是有點不一樣。有時候所謂的厭世,其實是出自對世間的愛,正因為有所期望,才會透徹失望。於是你厭倦,你吶喊,叫得聲嘶力竭,好像對一切都不再在乎,心坎裡卻還是等著有人能夠聽見自己的絕望。
我在等的那部車呢
它會不會又拋錨了
我在等的那個人呢
他會不會又不來了〈等〉
主唱巫堵和結他手筑筑亦曾就著「厭世」這一點作出過解釋,說草東雖然不少作品聽起來都很暴力(譬如〈情歌〉,他們也是近乎竭斯底里地吶喊著「殺了它 順便殺了我 拜託你了」),字裡行間也看似爬滿絕望,但其實他們真正想要傳達的事物都藏在字面之下,不但反暴力,歸根究底都是關於愛。簡單來說,若你在意的就只有殺或不殺,死或不死的那個層面,就永遠無法理解他們的音樂本質。
硬要形容的話,他們不是那種經過多重加工的精緻澱粉,而是徒手從土裡挖出的那顆馬鈴薯(我知道這實在是有夠古怪的比喻,但還是覺得很貼切),不該光用「粗糙」二字去形容,倒不如說,他們骨子裡本就自帶一種粗野以及暴烈,與天地共生,亦因此才顯得與制式化的人類社會格格不入吧。
我把故鄉給賣了 愛人給騙了
但那挫折和恐懼依舊 但那挫折和恐懼依舊〈情歌〉
派對之始
派對的開始,要從 2012 年說起,本為高中同學的巫堵和筑筑,同被陽明山上那人煙稀少且長滿芒草的草東街所啟發,繼而籌組了初代的草東,即「草東街派對」,早期的 dance punk 風格是受到電子搖滾樂團 Two Door Cinema Club 的影響,而後來成員幾經更迭,巫堵將樂隊名改為「草東沒有派對」,音樂風格也逐漸轉型到 grunge,就如同陪著他們長大的 Nirvana。
我想要說的 前人們都說過了
我想要做的 有錢人都做過了
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們虛構的〈爛泥〉
草東的歌曲結構往往並不複雜,但總會在和弦加入各種巧思,讓每首歌都耐聽且各具特色。歌詞則主要是從巫堵的個人經歷出發,像是獲得金曲獎最佳歌曲的〈大風吹〉,就是講他曾面對過的校園霸凌。另外有一首講愛情的作品〈在〉也是富含深意,從「我會一直都在」到結尾變成「我會一直都」,表達曾經信誓旦旦的承諾最終都淪為一場空話,簡單的減法,效果卻異常強烈。
他們從僅有幾百人的表演空間,到逐漸在大小場地都寫下爆滿紀錄,五年前甚至打敗五月天拿下了金曲獎的最佳樂團殊榮,被稱之為世代交替的一刻,而草東原本會在去年登上小巨蛋,寫下獨立樂隊史上的一頁光輝。
哭啊 喊啊 叫你媽媽帶你去買玩具啊
快 快拿到學校炫耀吧 孩子 交點朋友吧哎呀呀 你看你手上拿的是什麼啊
那東西我們早就不屑啦 哈哈哈〈大風吹〉
再沒有派對
凡凡離去以後,原定的小巨蛋演唱會宣告終止,他們的音樂救贖了無數迷途的人,卻終究沒能留住她。巫堵當時在沉澱一段日子過後說出:「只祈禱在世界的某個盡頭,會有人等著自己緩緩說道:『生命本就如此脆弱,萬物的死亡從不是結束,而是另種形式陪伴的延續。』大家都保重,要好好的,抱歉,謝謝。」,我們大概一輩子也無法學會好好道別,而這個曾說好要一起改變的世界還是一樣爛,只是,正因為帶著難以忘懷的遺憾與傷痛,至少有一點該學乖了,有甚麼想做的,想說的,真的別再等下次。
我聽著那少年的聲音 在還有未來的過去
渴望著美好結局 卻沒能成為自己〈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