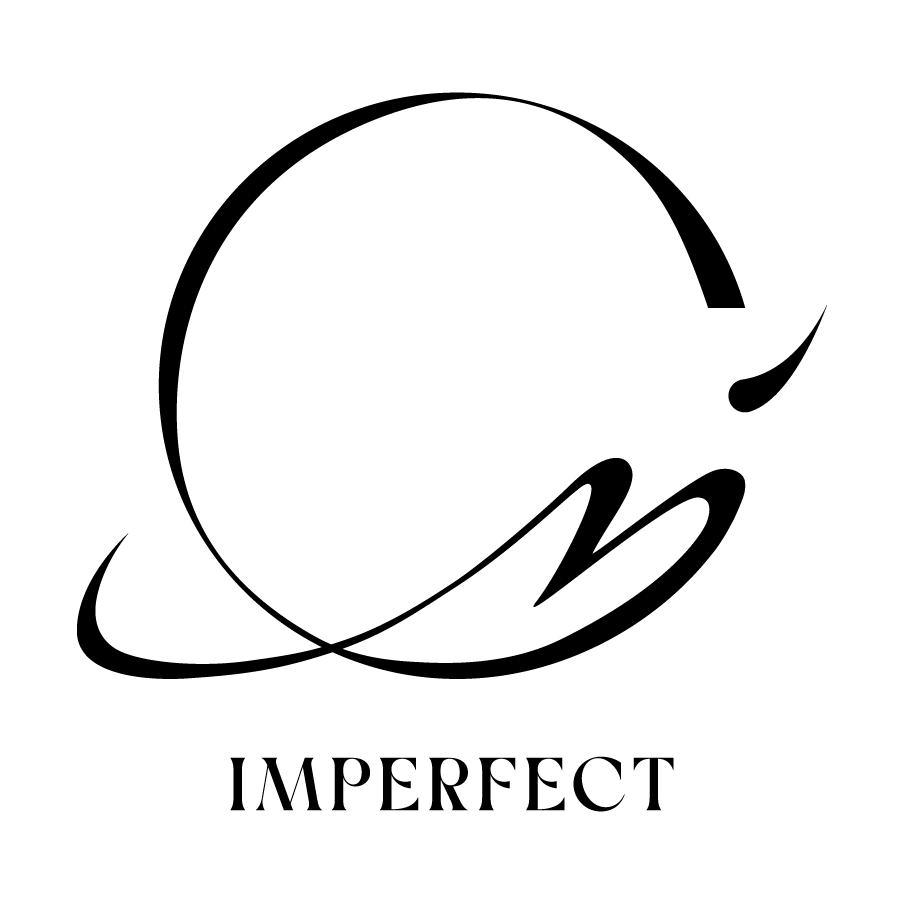來自盤古大陸的呼喊:「唯有戰勝恐懼,才有存活的希望。」 ── 恐龍的皮The Dinosaur's Skin
記得在我寫好訪綱的那個當下,看著那串洋洋灑灑卻帶點微妙的文字不禁失笑,這大概是我寫過最荒謬的一個訪綱了。然而,當那些問題套用在恐龍的皮(The Dinosaur's Skin)身上,卻又顯得如此合理。收到回覆後,眼前蹦出的第一句果不其然,非常「恐龍」 ──「最近債研究綁架偶悶ㄉ紙袋龍教背後ㄉ秘密!」,彷彿能看見三角龍那手舞足蹈的興奮模樣,嗯,這個訪問果然還是好荒謬。
以下便是我與從白堊紀穿越而來的兩隻恐龍的首次對話,正在讀這篇文章的你,如果越看越覺得莫名奇妙,沒關係,我們本就身處一個荒謬至極的時代,至少能和恐龍對話還是挺有趣的,對吧?
從恐龍視角看世界
恐龍的皮在 IG 自介上是這樣寫的:「找到…..世界喪剩下ㄉ恐農..」,去年因不明原因從遠古時代恐龍將要滅絕的當下穿越而來的暴龍與三角龍,在來到現代人類社會後決定組成樂團,以恐龍視角訴說他們的故事,並期望能夠找到其他倖存的同類。別看他們總是很鬧,會套個恐龍泳圈跑來跑去甚麼的(我也曾因為看到暴龍在演出時手臂上那個極盡霸氣的「群龍無首」刺青而笑歪),其實是相當有內涵的恐龍(我到底在說甚麼)。
至於許多人都好奇的兩龍真實身份,廣大樂迷也早有看破但不說破的共識,畢竟有時講得太白就不有趣了,他們就是恐龍啦(好不負責任的總結)。
當初接觸恐龍的第一首歌,是與甜約翰(Sweet John)及 I Mean Us 主唱兼鍵盤手 MANDARK 合作的〈Millions of Years Apart〉,也是他們在 Spotify 破百萬點擊的作品。遼闊又夢幻的樂曲,配上雖悲傷卻又不失浪漫的歌詞,帶領聽眾一起打開這封寫給百萬年前同身處於盤古大陸的夥伴們的情書,初次聽的時候便好喜歡。
人氣暴升中的兩龍,今年還得到了金曲獎的肯定,成為史上首組踏上紅毯的恐龍。三角龍這次便和我們分享了一段走紅毯時的有趣經歷:「沒有人教我們怎麼走,有點找不到路。暴龍看到黃宣的頭,一直在克制自己咬他的慾望。」嗯,我好像可以理解(誤)。
I will search the world for you
Cross the ocean or the Pangaea
I will spend my days waiting
Insignificant as we are
I love you
But we're millions of years apart〈Millions of Years Apart〉
人與龍
回到兩龍的近況,就是文章開首所提及到的,他們正在研究綁架他們的紙袋龍教(註:在七月於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舉辦《尋找恐龍的皮》專場前夕綁架兩龍的邪惡組織)背後的秘密,還有在寫一些新歌(重點),以及進行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計畫(或許是研究與遠古時空通話之類的?)。
紙袋龍教眾教徒
我問,當初在想組合名的時候,為甚麼會選擇著眼於恐龍的「皮」而不是其他部位?三角龍便說,原因除了「超讚」和「超酷」(我懂,像恐龍的腿聽起來就不太酷)之外,是因為他們在來到人類世界後發現,人類和自己也許並沒有那麼不同。
「不一樣的地方,好像就只是我們的外表,就只有這一點而已。」在截然不同的皮相底下,其實同樣藏著豐沛的情感,也同樣要面對生老病死,啊,還有暑熱。這兩顆多次在炎夏戶外賣力演出的恐龍的頭(沒錯,是頭,不是頭套),讓三角龍也不禁大呼:「夏天演出真的熱扁!以前恐龍時代好像沒那麼熱。」
看著兩龍之間的好感情,不禁想問,草食系三角龍與肉食系暴龍真的有辦法和平共存嗎?譬如意見不合的時候,難道不會打起來嗎?單就品種而言,感覺戰力有點懸殊啊。三角龍聞言表示,還好身邊的暴龍算是同類中性情比較溫和的傢伙,雖然偶爾還是會露出本性。
「可以和平共處的!但是也是會打起來… 有時候暴龍會來啃我的頭,我也會用角戳他,但還好都沒有弄到去醫院,大致上算是蠻和平的。」她說暴龍是個很好的聆聽者,不太會回話,但也許只是因為穿越過來後母語為英文(不要問為甚麼)的暴龍知道她聽不懂,才索性放棄對話了。「大部分時間,尤其在做音樂的時候,我們都是用那種,心有靈犀的溝通方式。」至少,聽起來是挺浪漫的。
Every dream you’ve had
Took us far into the unknown
But when I’m with you it feels like home〈Jurassic Ride〉
撫平傷痛的方法
前陣子推出的新歌〈Neck and Neck〉講共存,曲風一貫歡快,歌詞一貫幽默,但風趣的背後,其實也映照了人類社會的現況。「來到人類世界後,發現弱肉強食的戲碼正在人類之間真實上演,衝突與戰爭不間斷,恐懼在心中不停的滋長,我們都必須對抗自己內心的惡魔。因為唯有戰勝恐懼,才有存活的希望。」這首歌的創作動機,原本是來自他們在恐龍時代的生活經歷,像三角龍那樣的草食性恐龍,每天都要躲避肉食性恐龍的追趕,活在心驚膽顫之中,然而在意外穿越到現代後,卻發現其實人類之間也潛藏著相近的生存機制,物競天擇,正如香港某權威教授所言,要是沒辦法適應,很抱歉,你係要過身。
對兩龍來說,能讓物種與物種、種族與種族和平相處的方法,就是透過音樂。「我們在接觸到音樂之後,真正被音樂療傷。撫平了暴龍的怒氣,也擦乾角龍的眼淚。正因為感受過音樂的魔力,所以我們做音樂,希望藉此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世道混亂,在此期待兩龍成功感化世人的那天能夠快點到來。
Can't we just be friends
We can all camp under the moonlight
And just lay side by side, when the shooting stars light up the sky
If you don't mind
Then I don't mind〈Neck and Neck〉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記得初聽〈All My Friends Are Dead〉的時候,便覺得這個主題好有趣,後來才反應過來,原來這首歌是在哀悼他們那些在隕石撞地球時死去的恐龍朋友,只能說這兩人,I mean 兩隻龍,實在是太有才。
「每次想起隕石撞過來的那天,all my friends are dead,大家當時一定都感到很害怕,可能都還搞不太清楚就死了。天吶… 想到就好傷心。」他們表示,這兩年結交了很多人類朋友,實在不想再失去任何人了。而那份在同類紛紛死去時的孤寂感,其實也影射了現代人的社交孤獨,明明到處都是人,但我們卻依舊孤單。
When I saw a meteorite
Falling from the sky
Then I remembered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And I feel so lonely tonight〈All My Friends Are Dead〉
大滅絕倖存者的啟示
疫情久久不散,他們表示雖然沒有聽說會傳染給恐龍,但還是造成了生活上的很多不方便。經歷過大滅絕的光景,他們明白,死亡可以是一個瞬間的事,遺願這回事,在突如其來的災難面前,顯得太過渺小。「在我們的字典裡沒有遺願。因為活下來的每一天,都是我們多出來的。每一天都要當成在這世界的最後一天那樣活著。」不過,Bucket List 的話還是有的,就是…
「希望可以看到恐龍和人類共融的社會!」
「希望可以找到世界上剩下的恐龍!」
「希望可以去世界巡迴!」
作為史上第一爬蟲類團體以及從史前穿越過來的遠古生物,他們在現代人類社會的最大願景,就是能夠找到世界上剩下的其他恐龍,一起攜手共創一個人類與恐龍和平共處的世界。
If the smoke won't go
And the sea goes out of control
Let's go, no woes
I will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go
Wherever you go〈Take It Slow〉
快樂的氛圍 悲傷的故事
他們做音樂最初的出發點,是要療癒自己。「正因為知道悲傷很痛,寂寞很深,才故意讓音樂聽起來很歡樂。很多朋友在人類世界過得沒那麼順遂,所以會沈浸在我們的音樂裡,每次現場演出都能感受到大家的瘋狂和興奮。」台上台下一同進入一個沒有悲傷的時空,暫忘所有苦痛,盡情沈醉在音樂的美好中。片刻雖短暫,卻能永遠保存在心裡。
因此,音樂對他們來說也是抽離悲傷與苦痛的最有效解藥。「剛來到人類社會,發現恐龍們都滅絕了,真是無比哀傷!但無意間聽到一首歌,是來自 Dayglow 的《Dear Friend, 》,當下很像是乘坐在一朵雲上面,包覆我們所有的苦痛。嗚… 音樂最讚惹…」恐龍也讚,非常讚。
他們的作品融合了 Bedroom Pop、Indie rock、Dream pop、Synth pop、lo-fi 等多種曲風,創造出被稱為「遠古大陸的時空奇幻流行風格」的獨特路線,這時候兩龍的幕後推手 Skippy(脆樂團男主唱,也是恐龍們的製作人)出現,代為回答了一些技術層面的問題(脆樂團和恐龍的皮的末日合作曲〈Take It Slow〉也是無比精彩,樂迷們還為他們起了脆皮恐龍的暱稱)。
「一開始跟恐龍的皮相遇就發現彼此都很喜歡類似的曲風,Dayglow、Gingeroot算是創作啟蒙之一。在製作音樂的時候,希望能夠在快樂的氛圍裡說著有些悲傷的故事,搭配恐龍們特別的聲線,在復古與歪斜夢境中創造出了恐龍獨特的聲響。」於是他在恐龍的音樂中大量使用合成器和 detune chorus 電吉他的音效,最後還加上了恐龍的史前鳴叫,讓大家踏上遠古大陸的奇幻時空旅程。對於鳴叫的部份,三角龍就表示:「暴龍蠻擅長嚎叫的,我就不太會,叫的比較難聽,很傷(喉嚨)。」
對他們來說,創作最大的困難和目標,都是希望人類能夠對恐龍的故事產生共鳴。不管是《All My Friends Are Dead》暗喻現代人的孤獨;《Neck and Neck》把與心魔對抗的過程用肉食恐龍來比喻;還是《Take It Slow》以不同生物的觀點探討「生存」,都是他們為了讓人類與恐龍更為了解彼此的創作。
恐龍的感染力毋庸置疑,說的不止是在音樂上。比方說,在我跟經紀人來回確認著內容細節的時候,到最後都開始用恐龍貼圖來對話了,看來在完成這篇文章後,我可以先去把加入紙袋龍教的申請給遞一遞了。
last but not least…
最後有點好奇,穿越過來後你們有看過電影《侏儸紀公園》嗎?
:有的。《侏羅紀公園》只看了第一集,有點怪怪的。《侏羅紀世界3》也有去電影院看!但也怪怪的。可能他們都是基因改造的恐龍,所以長得和印象中不太一樣。
「世界壞了,但我在這。」
photo via The Dinosaur's Sk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