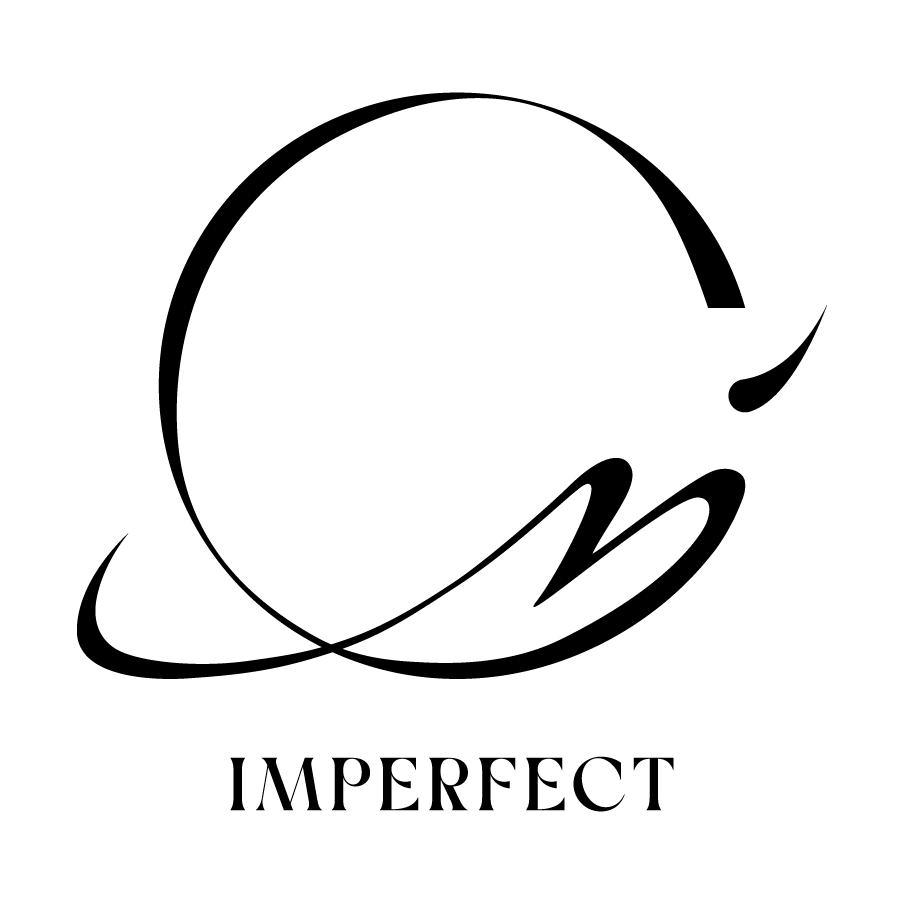亞洲電影大獎|「真相就是真相,沒有痛苦或快樂之分,it is what it is。」── 阮鳳儀
在促成這次訪問之前,對於《美國女孩》,我其實一直都是處於想看卻又不敢看的狀態,正如導演阮鳳儀(Fiona)所講,《美國女孩》是許多亞洲家庭的縮影,我們都不多不少會在這部電影中,窺見到過去某個部份的自己。再加上,我光是看那些相關的網絡文章就已經淚崩了,看電影的話不知道要準備幾張紙巾。直到確認會跟阮導在亞洲電影大獎那天進行訪談,我才總算下定決心,在準備訪綱前把電影看了一遍。果不其然,好幾次都被那精準的對白狠狠刺中內心,白馬那段哭到不行,但看到最後,我好像也隨著芳儀和莉莉的和解而稍稍釋懷了一些甚麼,具體說不上來,但心中的某個部份確實有變得比較舒坦了。
「在這個世界上,我最不想成為的人是我的母親,因為她的恐懼,會成為我的恐懼,而她的軟弱會使我軟弱。」
《美國女孩》
~ IM with 阮鳳儀 ~
小時候覺得父母好像無所不能,甚麼事情都有辦法解決,是生活中最堅固的一座靠山。長大後發現,啊,原來他們跟我一樣,其實都是一個有血有肉,不那麼完美的大人,他們也有情緒,有脆弱,很多的脆弱。
大多數父母,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以內給予了孩子全部,只是許多時候,那些愛與奉獻,和我們所期望的不一樣。創作《美國女孩》的過程,是阮導放下過去的方式,她一路走過來了,那我們每個人,相信也會有至少那麽一個,能夠跨越傷痛的機會吧?
IM:Imperfect Mag
F:阮鳳儀(Fiona)
IM:這次來香港參加亞洲電影大獎,除了頒獎典禮之外,你最期待的事情是甚麼?
F:其實我來香港蠻多次了,之前因為朋友拍片,有來住過大概一、兩個月的時間,所以我覺得最期待的事情,應該是回去造訪以前覺得很好吃的餐廳啊,或者小吃店這樣。
IM:在你眼中香港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F:我覺得就是很有都會感吧,跟台北比起來的話,所以我覺得其實走在路上就蠻有趣的。
IM:許多看過《美國女孩》的人都形容這是一部後勁很強的電影,那你自己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在這部作品面世後,有沒有為你帶來一些意料之外的影響或思考?
F:跟觀眾一起看的時候,我覺得會用不一樣的眼光去看待這部電影。當然我們一直都希望去追求跟觀眾有最大程度的共鳴,上映後我也看了很多人所寫的,關於他們自己的故事,這個部份其實是我當初沒有預料到的。然後,我在讀那些故事的時候,也會被他們的家庭故事所感動吧。
IM:透過大屏幕再看一次這部電影,對你來說是怎樣的感受?
F:因為在剪接和後製的過程中,我已經看 100 多次了,所以…(笑)。不過我覺得如果現在再看的話,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吧,畢竟也已經過了一兩年了。
IM:透過電影從第三身的角度去看過去的自己,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將自己的故事拍成電影,對你來說除了是一個釋懷的過程,當中還有沒有伴隨一些焦慮或不安?
F:這其實是很多家庭的故事,我覺得應該要坦承的去面對。有些人會覺得寫自己家庭的故事好像很私密,然後會害怕把它講出來,可是我的不安感不是來自那裡。編劇時的焦慮,主要是來自於想要把這個故事講得夠深,或者能夠去同理每一個角色,而不是說去輕易的塑造誰是壞人,或誰做得不好,並不是用一個批評的角度去講這件事。
IM:寫這個劇本的時候剛剛開始 COVID,而故事的時間點是落在 SARS 的年代,你會不會也覺得,啊怎麼那麼剛好又是差不多的情況?
F:有有有,當然這對世界來說是一個不好的事情,是不幸的事情,但那時候我確實會覺得,欸,怎麼冥冥之中它又再發生了。
IM:你曾說過因為疫情的關係,你們全家又再次被關在了一起,那這一次,家裡的氣氛有怎樣的轉變?
F:有,我覺得以前大家經歷過了,然後這一次 Covid 就是媽媽沒有在生病的狀態嘛,所以我覺得這也是給全世界一個休息和喘息的空間吧,就想一想我們到底想要過甚麼樣的生活。
IM:在電影的最後,芳儀透過請媽媽幫自己掏耳朵去講出一些心底話,你當初和家人關係好轉的契機也是這樣的嗎?
F:現實生活當然沒有像電影裡掏掏耳朵這麼簡單就過去,我覺得都是隨著年紀的增長吧,因為我在寫劇本的時候,剛好是從 29 歲跨越到 30 歲,雖然只是一年的差距,但感覺還是蠻不一樣的。就是當自己也開始考慮到要結婚啊要有家庭,就比較能夠去同理做父母的為難處吧。
IM:你覺得現在的自己已經放下這個課題了嗎?
F:我覺得放下蠻多的,嗯。
IM:看過《美國女孩》後,爸爸媽媽和妹妹有沒有說些甚麼?
F:那個,妹妹覺得自己的戲份太少了(笑)。爸爸覺得則是覺得,家裡雞毛蒜皮的事情你還可以寫成這樣,不容易啊之類的。然後,我覺得媽媽的感觸應該更深吧,她在裡面的戲份也最多。
IM:那段經歷對爸爸來說,相對沒有像你和媽媽那樣深刻嗎?
F:我覺得可能角度不同吧,在這個電影裡面爸爸也是一個蠻左右為難的角色。
IM:妹妹現在也結婚了,自從不再住在一起後,你們的關係有再變得不同嗎?
F:當然啊,不住在一起就很少機會吵架啊(笑)。
IM:看著梁芳儀所經歷的那一切,你是否也重新認識到少女時期的院鳳儀?
F:嗯… 其實我覺得在寫角色的時候,我就已經把她分割出來了。每一個角色都有帶著我的成份,不止是芳儀。對我來說,她已經轉化成一個新的人物了,所以我不會覺得,我是在看待「我」。
我看這部電影最大的感受是來自於,國中時期算是我比較痛苦和難熬,然後覺得很漫長的一個人生階段,有時候你不知道為甚麼這些事情要發生,但當你將它戲劇化,把它變成作品,它可以被分享的時候,它的發生就變得有意義了。
IM:芳儀和白馬,莉莉和芳儀,你覺得我們如果想要學會愛,就得先要面對絕望嗎?
F:其實我不會覺得芳儀遇到白馬那件事情是絕望,而是要學會不要想去控制。當我們有想要控制的心情的時候,不論是對馬或是身邊的人,往往只要對方不符合我們的想像,我們就會很容易 feel disappointed,所以我們應該是要學會去接受那個現狀吧。
「妳到底在氣妳媽什麼?」
「我只是覺得…她可以再做得更好。」
「但如果這已經是她的最好了呢?」《美國女孩》
IM:你是在甚麼時候發現這件事情的?
F:應該也是蠻大之後吧,大概也是 29 到 30 歲左右。
IM:在那個無法理解亦不被理解的人生階段,陪伴或為你帶來一絲慰藉的是甚麼?
F:國中到高中比較是書,就是文學吧。高中的時候蠻喜歡詩的,然後到了大學才比較有時間看電影,也喜歡小說。
IM:之後也會想要向寫小說或詩發展嗎?
F:不會,作家太不賺錢了,覺得會活不下去(笑),還是做影視創作好了。
IM:你曾說過,《美國女孩》就是很多亞洲家庭都會經歷的故事,那根據你的經歷,你認為我們該如何跨過那些來自原生家庭的創傷,那感覺好像永遠也跨不過去的坎?
F:我覺得很多人對於原生家庭啊,或是說那些不愉快的經驗,要嘛就是逃避,要嘛很渴望和解,覺得為甚麼我們不能坐下來好好的和解呢。可是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它是花了很多很多年去累積的,若我們去期待它在一夕之間解決,其實很不切實際。我曾讀到一個蠻有趣的的說法,就是要 get over 一個 relationship,至少需要那個 relationship 的一半時間。
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應該就是要去嘗試,因為與家人和解這件事是需要雙方,或是 multiple,大家都要 be ready for that,但那是很難很難的。我甚至有聽過,有些人會以為自己會和長輩在病榻前來個大和解,結果卻完全沒有發生,然後對方就過世了,他就覺得非常的 disapointed,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it may never happen。
IM:那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還能夠做些甚麼去修復那些關係和創傷?
如果真的想要去做些甚麼的話,我覺得就是回到剛剛說的,你要去理解,你只能單方面的先嘗試去理解,去接受,他就是這樣子。當然,有時候的不能理解或不能接受,是來自這個人的這些行為,曾經帶給你很多的傷害,所以我們其實也是不能接受為甚麼這些傷害會被造成。但我覺得要改變的話,就得先從自己開始,而那其實是相當花時間的。
IM:現在的你跟媽媽之間的相處是怎麼樣的?也會聊心裡話嗎?
F:我覺得她有比較接受我也是一個成人了。以前很多的爭執是來自於,她覺得「喔,你是我的小孩」,然後我記得我跟她吵架,我說我已經快 30 了,我不是一個小孩這樣。所以現在好很多,比較能夠平等的溝通,理性的溝通。會聊心裡話啊,然後每個禮拜都會見面。
IM:你曾說現在的你已經明白一切其實就只是一個過程,這也是你在 29、30 歲的階段學會的事嗎?
F:對,我覺得拍電影讓我學到很多,包含去念電影研究所的時候。It’s a lot of team work,然後你會發現,很多事情你都無法控制,就算作為導演也是一樣。你只能去 work with what you have,然後一直去接受各種的困難和挑戰。我覺得這有讓我更快的去領會到,這一切其實就是一個過程,嗯。
IM:拍電影是你跟自己的內在小孩和解的方式嗎?
F:我覺得所有的創作都一定帶著療癒的成份,但我覺得不只是這樣而已。如果只是自我療癒的話,有時候我寫一寫東西其實就可以了,我覺得電影最重要的是可以讓我們 connect with other people。
IM:今年會有新的作品嗎?
F:有的,有些正在寫,但因為最近一直出國(笑),所以就很希望之後可以坐下來好好的寫作這樣。
IM:如果要在「痛苦的真相」和「快樂的假像」之間選擇一個,你會怎麼選?為甚麼?
F:我覺得它們兩個其實就是 flip side of the same coin,就是一體兩面。所以… 我不會覺得真相一定痛苦,真相就是真相,沒有甚麼痛苦或快樂之分,然後,假像也不一定是痛苦或是快樂的。我會盡量 neutral 地看待這件事情,嗯… 該怎麼講,就是我覺得如果很中性的去看待事情,它就沒有所謂的正向或負向,it is what it is。
IM:你現在看待事情也是用這樣的方式嗎?
F:嗯,就是盡量不要帶那麼多的情緒去看事情吧。
IM:你本來就是一個比較理性的人嗎?
F:沒有,以前我是一個蠻情緒化的人,甚麼事情都帶著強烈的情緒。可是這樣子的話,一來 you can’t really see things clearly,二來就是其實你會讓自己很痛苦。
IM:對現在的你來說,溫柔是甚麼?
F:我覺得溫柔就是,a lot of effort,and a lot of strength。就是我覺得,如果你軟弱的話,是沒有辦法溫柔的。那其實是一種,你要很有力量,很有自信,才有可能是溫柔的。
IM:你覺得自己現在的心靈足夠強大了嗎?
F:我覺得應該可以更強大吧(笑),現在還 ok。
producer Ruby Leung
photographer Sam Tso, assisted by Tim Chan